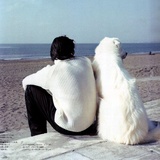嘉慶帝在親政的第6天就下令革職賜死了“清朝第一貪官”和珅,更是在任上,剿滅了在全國各地起義的白蓮教。
可就在這樣一位英明國君的帶領下,清朝還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發展遠不如乾隆時期,這是怎麽回事?

«——·墨守成規的嘉慶帝·——»
嘉慶帝是位保守的皇帝,熱衷效仿“祖宗成法”,以“法祖”爲己任,缺乏創新和突破“祖宗成法”的勇氣和毅力。
嘉慶帝禦制的《守成論》十分全面地展示了他墨守成規的性格特征。

一方面,嘉慶帝感念先祖創業艱難,過度崇拜和依賴祖輩們創立的制度和規則,嚴重缺乏打破陳規舊俗的勇氣和決心,以繼承祖制爲己任,對祖宗成法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保持高度自信。
另一方面,嘉慶帝將改革視爲洪水猛獸,堅信王朝中葉之主若是心存改革之念,定是聽了因貪功谄媚之臣的慫恿。

如果人君聽信讒言,推行改革祖宗成法,不僅無法建立有效的規章制度,還會導致國家動蕩不安,還將曆代亡國的根源歸結爲亡國之君們不肯守成。
嘉慶帝自诩心存壯志,立志要成爲一代明君聖主,自然不會效仿亡國之君“不肯守成”的做法,而是要堅持墨守成規,在位期間盡可能地保守爲政,不遺余力地效仿“祖宗成法”。

如果說《守成論》僅僅停留在思想理論層面,那麽嘉慶抵制海運的事迹就是很好的實例證明。漕糧是我國封建王朝時期由江蘇、浙江、安徽等東南地區運輸到京城的稅糧。
漕糧運輸方式分爲河運和海運兩種。清朝入主中原後,統治者承襲明制,繼續以河運爲“正載”。

嘉慶十六年(1811),“黃水高于清水五尺有余,而下遊將近海口之大淤尖地方,又形淺滯。
即使本年糧運,尚可勉強通行,日久終恐贻誤,不可不豫爲之計,因思海船試運一事。”黃河淤堵嚴重,內河航運受阻。漕運涉及錢糧,影響國計民生,情況以不容樂觀。
“爲了順利運輸漕糧,而花費巨額款項治理河道”。針對此,相關官員提出用海運代替漕運。

對于此等“挑戰”祖宗成法的計劃,嘉慶帝和兩江總督鐵保等臣子商討後,列舉出“海道極險之處”、“海行欲避外洋之險”、“海行風信靡常”、所需經費“必甚浩大”、船只建造和使用問題、水師所需糧饷等不可行者十二。
君臣們從地理自然和經費使用等諸多角度分析實行海運的利弊。然而,最終真正說服嘉慶帝堅持河運,抵制海運的關鍵原因是“漕運惟元至元十九年始爲海運,至明永樂十三年而罷。”

嘉慶帝面對需要變更祖宗成法的重大決策時,最終還是選擇了退縮,聲稱:“漕運由內河行走已閱數百年,惟有謹守前人成法。將河道盡心修治,河流順軌,則漕運按期遄達,原可行所無事。即萬一河湖盈绌不齊,漕船不能暢行亦惟有起剝盤壩,或酌量截留,爲暫時權宜之計,斷不可輕議更張,所謂利不百不變法也”。
因爲河運是前人成法,已經奉行數百年,不可輕易摒棄,所以嘉慶帝妥協了,堅持繼續推行河運,酌情將海運作爲權宜之計。

«——·優柔寡斷放過余孽·——»
在封建王朝,地方錢糧是否能按時按量入庫關系到國家財政稅收是否穩定,也是衡量一個王朝經濟實力好壞的重要標准之一。
清朝各省虧空之弊源自于乾隆四十年以後。嘉慶即位後,“這種虧空的狀態不僅仍然無法扭轉,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成爲清王朝衰敗的最典型表征。”

面對日益嚴重的財政虧空,嘉慶帝卻“拿出更嚴厲的措施去進行整治。可是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卻是猶豫不決,縮手縮腳,”缺乏決斷。
在整治地方虧空這一問題上,嘉慶帝盲目采取“徐徐辦理”、“緩緩歸款”的態度,將查清虧空看作與官民爭利,畏首畏尾,嚴重欠缺一個合格帝王該有的果斷和雷厲風行,給予地方貪官汙吏喘息的余地,“在客觀上卻起著助長、縱容虧空的作用。”使得百姓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嘉慶十八年(1813)七月,直隸教首林清、山東教首馮克善、河南教首李文成三人在河南道口扛起反對清政府統治的大旗,決議將三地的八卦教聯合起來,成立爲“天理教”,也就是白蓮教的一個分支。
九月十五日,趁嘉慶帝離京東巡之際,天理教首領林清、李文成等人借機向京城這一首善之地發起進攻。

約兩百名教衆進入宣武門後,在太監接應下,迅速分爲兩路,向紫禁城內進發。一路由陳爽帶領約三十名教衆,在太監劉金等引路下,進攻東華門守門官兵。
另一路由陳文魁、劉第五帶領約五十人,與宣武門外假扮商販,在太監張太等人接應下進攻西華門,並趁勢反關城門後,長驅直入。最終天理教寡不敵衆,不久後便被清軍鎮壓,起義以失敗告終。

天理教信衆人數不多,但涉及多省。民間勢力進攻京師腹地,且是封建王朝曆史上首例民間宗教勢力公然闖入皇宮,意圖奪取政權的重大曆史事件,可謂是“漢唐宋明未有之事”。
此事影響極爲惡劣。最終捕獲人數和攻門總人數並不相符。對此,嘉慶帝確不敢放松警惕,下令清查散落民間的天理教余孽,以絕後患。

可是後來,嘉慶帝卻自食其言,既想要“蕩清寰宇”,又想感念“鄉愚無知”,無視身爲人君的威嚴,親手推翻自己的政令,做不到言出必行,顧此失彼。
至使嘉慶二十五年(1820),也就是嘉慶帝在位的最後一年,“逆案內最要次要五十余犯,指名饬拿,總未報獲,京城本年春夏以來,曾緝獲數名”,時隔多年,天理教清理竟還未徹底清理殆盡。

和珅是乾隆帝時期的大奸臣,而富察·福長安“與和珅朝夕聚處,于和珅罪狀,知之最悉”,不僅如此,他自己也是個中飽私囊的奸臣。
嘉慶帝繼位後,很快就將和珅和富察·福長安抄家逮捕,並表示要秋後處斬,手段之雷霆百姓們無不拍手稱快。

可沒想到,僅僅幾個月之後,嘉慶帝突然覺得富察·福長安所貪汙的金額不過是和珅的十分之一,不足以判處這麽大的懲處,最終竟然將他放了。

嘉慶帝在任上看似做了不少有利于大清安穩的事,但這些事不過就是在延續過往的政策,但是朝代發展的內容變了,以前的措施怎麽能後直接拿來用呢?
而他本人的性格優柔寡斷,對于邪惡勢力不能做到斬草除根,也使得清朝積弊甚重,終難逃頹廢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