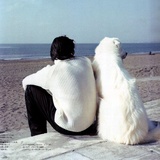公元前251年,燕趙兩國軍隊在趙國的鄗地進行了一場激烈的搶殺。
剛開始,燕國信心滿滿的攻打趙國,一致認爲能將其拿下。
但令人想不到是,關鍵時刻,廉頗率領趙軍猛攻燕國,以區區數萬的兵,戰勝了燕國數十萬大軍。
後來,這場戰爭不僅成爲了典型的以少勝多的戰例,更是被記載有史以來的大規模戰役。
那麽,趙國是如何反殺的燕國?這個典型的案例又帶來了哪些影響?

«——·戰爭的背景及經過·——»
戰國後期,強大的秦國采用“遠交近攻”的策略,即遠交齊、楚,而近攻三晉韓、趙、魏,以集中主要兵力,各個擊破山東六國,最終完成統一大業。在三晉中,此時又以趙國最爲強大,它“嘗抑強齊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所以,秦國視趙國爲頭等進攻目標,而秦、趙之間的戰爭自然也不可避免的。
公元前260,趙國國君孝成王中了秦國反間計,以只會紙上談兵的趙括取代老將廉頗,致使長平之戰輸得慘烈,四十余萬將士被活埋,自此,趙軍的主力折損殆盡。

此時的燕國,自昭王改革以後,也是人才濟濟,國庫殷實,兵強馬壯。燕昭王在位時雄心勃勃,意圖逐鹿中原。爲報齊國武力幹涉燕國內政之仇,曾派大將樂毅領兵攻下齊國七十余座城市,使得強大的齊國元氣大傷。
雖然齊國的反擊使得燕國國力受挫,但燕國畢竟還是一個頗有實力的一個國家;盡管昭王之後的國君無論在識見、才能還是魄力上也都略遜一籌,但是同樣地,他們也都沒有放棄對外擴張、壯大燕國的主張。所以,他們一直密切關注時局變化,等待時機。

公元前256年,燕國趁趙長平之戰後無暇顧及之際,攻占了趙國的昌城(今河北冀州西北),激化了燕、趙矛盾。爲進一步刺探趙國虛實,公元前251年,燕王喜以與趙修好爲名,派相國栗腹出使趙國,送趙王五百金爲壽。
回國後,栗腹便建議燕王:“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燕王喜在諸多佞臣的逢迎之下,聽不進昌國君樂閑、大夫將渠的悉心分析和懇切勸誡,組織起數十萬大軍,兩千乘兵車,分作兩路,浩浩蕩蕩南下:栗腹將四十萬攻打趙國鄗地;卿秦將二十萬攻打代地。
燕王自己又親率一支偏軍在後面接應,以爲憑借著數倍于趙軍的兵力,就可以一舉拿下趙國。

爲抗擊來犯的強敵,保護自己的家國,趙國上下一心齊動員,很快征集起數萬兵衆,由老將廉頗率軍八萬在鄗城迎擊栗腹的燕軍。他利用栗腹本非將略之才,卻好大喜功的特點,先隱其精銳,示之以老弱疲憊之卒,誘栗腹孤軍深入,再以精兵強將橫向殺出,打燕軍一個措手不及。
一番激戰後,栗腹被擒殺。進而卿秦、樂乘在代地被趙軍擊敗,駐守清涼山的樂閑也隨即降趙。兩支大軍的慘敗,使燕王喜驚恐不安,倉惶逃往燕都。
廉頗則率趙軍乘勝追擊,一度深入燕境500裏,包圍燕都,直到燕人答應趙國所提條件,才解圍而去。

燕王喜發動這場侵趙戰爭,志在必得,欲憑強兵攻下趙國,進而兼並其他諸侯,建立不朽勳業。
不想,鄗城一戰,就使他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輸得如此之慘!而趙國在強兵壓境、國家命懸一線的險地,借此卻以少勝多,以弱克強,轉敗爲勝,化險爲夷!應該說,戰爭結局,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然而雙方或勝或負,看似偶然,背後卻也蘊含著必然性的原因。
«——·戰爭勝負的原因分析·——»
首先,戰爭的性質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雙方的勝負。
從戰事全局來看,燕國是趁人之危,發動的是侵略性的、非正義的戰爭。俗語講,理直才能氣壯。這就注定燕軍相對于趙軍而言,必然將、帥不諧,士氣低落,戰鬥力不足。這一點從戰前君臣對話中也能看出端倪。而一旦遭遇抗擊,軍隊必然是無心戀戰,丟盔棄甲。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趙國軍民在關乎國家安危,政權存亡的戰爭面前,英勇抗擊來犯之敵,便是正義性的抗爭,是愛國主義的真情流露和體現。兵法上講,臵之死地而後生,大敵當前,大家同仇敵忾,軍隊將帥一心,士氣高漲,以一當十,戰鬥力自然強大。

其次,最高當權者的兼聽與偏信,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燕王喜在栗腹等人的煽動下,內心的那種征服趙國、進而一統天下的欲望,就一發不可收了。
他根本聽不進任何正確的建議和意見。當樂閑告誡他:“趙四戰之國,其民習戰,不可伐”時,他則說,我以三倍之衆、五倍之衆討伐它還怕打不贏?最後還憤憤地說:是不是因爲你父親樂毅的墳墓在趙國才不願意發兵趙國?大夫將渠勸他說,你才派人與趙國通好,還送趙王五百金壽金,轉眼就進攻人家的國家,這是不祥征兆,一定不會成功的。他不僅不聽,反而決定親率偏軍隨大部隊出發。
情急之下,將渠抓住國王腰間結系印紐的绶帶以阻止其上車,沒想到燕王喜“以腳蹴之。”將渠哭著說:“臣非以自爲,爲王也!”但終不能阻止燕王盲目的行動。燕軍敗北、樂閑一氣之下奔趙後,燕王喜才有所醒悟,遺樂閑書信以謝罪。但悔之已晚。

趙王在得知燕國大軍壓境時,也曾一度慌了手腳。但他急忙召集了群臣來商量對策。想必當時趙國朝廷之上也是七嘴八舌,亂作一團。
此時的趙孝成王應該是認真聽取了各方意見,斟酌之後,最終堅持並采取了正確的意見,果斷進行安排部署,一邊動員全國民衆,大家上下一心,頑強抗擊來犯之敵;一邊決定重用老將廉頗,任其放手調遣、指揮軍隊,這才有了這個一戰而扭轉戰局的機會。

再次,將帥的戰略戰術思想,決定戰役的成敗。
燕國丞相栗腹銜王命、領重兵,可謂志得意,自以爲此一去必然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所以,戰前,他沒有整體戰略部署,用備不虞;戰鬥中,又求勝心切,戰術失當,中計受騙,導致燕軍潰敗,一瀉千裏,自己也落得個身首異處的下場。這也是驕兵必敗的一個例證。

與燕國相反,當得知燕軍已經侵入到宋子時,在邯鄲的趙國君臣情急之下,積極商討對策。鑒于長平之戰對趙國軍隊的嚴重削弱,趙王在全國範圍發起緊急征兵令,號召國人保家衛國,共同抵禦來犯之敵。很快就組建起一支數萬人的軍隊,交由老將廉頗統帥指揮。

廉頗骁勇善戰,作戰經驗豐富。他清楚這支由老弱病殘倉促間組成的隊伍,如果與強大的燕軍鬥勇,無異于以卵擊石,螳臂擋車。不能硬拼,只能智取。他仔細地分析了燕軍情況,並充分利用了栗腹好大喜功、求成邀功的心理,在雙方交戰中,先示弱于彼,進一步激起其驕狂,引誘他狂追不舍,繼而以精銳伏兵四起,圍而殲之。

正是戰前周密的部署、知己知彼的分析,戰鬥中機動靈活、虛虛實實的戰術運用,才創造了趙軍以少勝多、以弱克強的戰爭奇迹。
«——·鄗之戰的社會影響·——»
鄗之戰的勝負,對燕、趙兩國都有很大的影響。
首先,對于燕國而言,戰爭的慘敗嚴重削弱了它的國力,遏制了它向中原地區發展的勢頭,其發展曆程自此由盛轉衰。

燕國是西周初年開國奠業的重臣、姬姓貴族召公奭的封國,是周王室的北藩屏障。其疆域大體包括今天的河北北部、北京地區及遼西的大淩河一帶,周圍多分布著東胡、山戎等各個少數族,東南與齊鄰接。
西周春秋時期,中國的政治文化重心在中原一帶,因地處偏遠,此時的燕國,與西周王室和中原各國交往較少,所以,《春秋》經傳、《國語》等文獻都少有記載。

今天在北京地區和遼西等地發現有大量西周時期的燕國貴族墓葬和窯藏銅器,這些考古成果證明了燕國此階段雖不爲中原諸國所熟知、但在冀北、遼西地區卻一直存在、延續和發展的情況。如北京昌平縣白浮村西周墓,遼甯朝陽魏營子九座土炕木椁墓,遼甯淩源馬廠溝及其附近的喀左北洞村和山灣村的窯藏銅器等。

可以說,燕國紮根于此,一方面少了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爭霸鬥爭的沖擊和消耗,自然完成了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社會形態的更叠,且姬姓諸侯依然掌控此地最高權力。
另一方面,在與少數族長期的紛爭與融合過程中,既利用、發揮了中原農耕文明先進的文化理念,又汲取了北方少數族的遊牧文化之特長,其實力是在不斷發展壯大,以至于進入到戰國時期,尤其經過昭王的改革之後,逐漸發展成爲中國北部地區最強大政權,崛起爲戰國七雄之一。
燕國延續了800余年而中無斷絕的悠久曆史,以及其文化體系中糅合的少數民族草原遊牧文化因子,都是戰國七雄中獨有的,也是其旺盛生命力的體現。

強大起來的燕國,自然意欲沖破地域的局限,與其他國家一爭高低。所以長期以來,一直對中原地區虎視眈眈,伺機發起征服他國的兼並性戰爭。
鄗之戰可謂燕國史上的一個分水嶺,之前是它的發展上升階段,之後便是它的衰落期了。

燕國統治者原本以爲這次可以一舉拿下趙國,爲它之後的兼並戰爭開辟道路,卻不料初露鋒芒,便遭當頭棒喝:軍隊潰敗如山倒,將帥或死或亡,連國都都幾乎不保。
短暫的解圍之後,第二年、第三年,接連遭到魏、趙兩國的聯合圍攻。國力的嚴重損耗,使燕國隨之而來的幾年間,元氣一直不能恢複。
雖然,在此期間,趙國自身不斷遭到秦國的侵犯,喪師失地,但是在燕、趙關系方面,依然占有一定的優勢,公元前243年,廉頗之後的又一趙國名將李牧率軍攻燕,奪得燕國的武遂、方城兩座城池。

由于此時趙國一再受困于秦國,其原來的統帥廉頗也已客死楚國,而新統帥龐煖又與自趙來燕的劇辛曾經關系很好,所以,燕王喜想當然地認爲,反攻趙國的機會來了。于是便與劇辛商議。
劇辛可謂是第二個栗腹,同樣的自以爲是、盲目自信,誇下海口:“龐煖易與耳!”公元前242年,燕王喜又犯了當年同樣的錯誤,輕率地讓劇辛領兵攻打趙國。
結果是龐煖指揮的趙軍獲勝,劇辛被殺,燕軍兩萬余人被俘獲。再次遭受打擊的燕國自此更加被動,再沒有任何的反擊力量了,公元前236年,任由趙國又攻取了它的漁陽城。之後,燕國苟延殘喘,直至公元前222年被秦滅掉。

其次,鄗之戰,對趙國而言,不僅是實力的嚴重損耗,也是加速其滅亡的推助劑。
雖然這次戰爭,趙國獲得了軍事上的全面勝利,但戰爭的殘酷和物資、人員的嚴重損耗,對于剛剛經曆過長平之戰沉重打擊的趙國而言,無疑于雪上加霜。
戰前,趙國最大的敵人就是秦國;戰後,趙國便一方面要隨時防範燕國故伎重演,進行反攻,另一方面,又承受來自秦國的強硬攻勢。
抗擊秦國的一次次失利,使趙國轉而加強對燕國的打擊和壓制,這樣一來,自然又削弱對秦國的抗擊力量。在腹背受敵,心分兩處的艱難處境中,趙國偏既遭天災,又遇人禍,昏庸的統治者聽信讒言,自毀長城,誅殺良將李牧,終于使趙國在惶惶中走向了它的末日。

此外,這場戰爭還影響了當時整個中國的時局。
戰國後期,隨著秦國勢力的快速增長及其對外的不斷攻伐,山東六國普遍感到驚恐不安。于是他們不惜重金,招賢納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結成抗秦聯盟。六國中,謀臣、良將荟萃,地域廣闊,士卒衆多,他們“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
但由于這只是個非常松散的抗秦聯盟,各國都想在其中實現本國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一旦有利益沖突,彼此免不了會互動幹戈、兵戎相見。燕、趙之間的這場戰爭,便是最好的例證。
而這種內讧和戰爭的自我消耗,便于秦國坐收漁翁之利,有助其兼並戰爭的快速推進。正如賈誼《過秦論》中所言:“秦無亡矢遺镞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于是縱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伏,弱國入朝...”

所以,從局部來看,就燕、趙兩國而言,這場戰爭的結果無論勝負,都是災難。不僅是對本國人、財、物的嚴重損害,而且是政權走向滅亡的拐點。但若從長遠和全局看,它加劇了各諸侯割據政權的消亡進程,有利于秦國的統一戰爭,對于整個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創造了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