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突破田家鎮、半壁山防線後,水師前隊于鹹豐四年十月十九日(1854年12月8日)駛至九江江面。
這時,太平軍主力大部集結于長江北岸黃梅一帶。
黃梅地處鄂、贛、皖三省之中樞;東可屏蔽安慶,南可支援九江,西可反攻武漢。秦日綱固守黃梅,將城牆增高數尺,滾木擂石,四面環布。
鹹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12月23日),湘軍與荊州清軍會攻黃梅,太平軍戰敗,放棄縣城,一部分退駐安徽省宿松、太湖,大部分退駐孔壟驿、小池口。秦日綱苦心經營的黃梅要塞體系迅速瓦解。
鹹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1855年1月1日)夜太平軍棄守小池口,主力撤入安徽境內,羅大綱則率部千余渡江,撤至江西湖口縣。
當時曾國藩趾高氣揚地宣稱:“長江之險,我已扼其上遊,金陵賊巢所需米石油煤等物,各路多已斷絕,逆船有減無增,東南大局,似有轉機。……臣等一軍以肅清江面,直搗金陵爲主。”

曾國藩
他在做著“直搗金陵”的美夢,豈知一場慘重的失敗就要來臨。
九江之戰早在鹹豐四年(1854年)10月,太平軍放棄武漢,退守田家鎮時,楊秀清決定重新組織強有力的西征指揮部,派石達開抵安慶,主持上遊軍事。
此時,曾國藩也由田家鎮進抵九江城外。石達開鑒于湘軍士氣正盛,水師更占優勢,便決定扼守要塞,伺機打擊敵人。于是,他親自坐鎮湖口,林啓容力守九江,羅大綱據守湖口對岸之梅家洲。曾國藩爲集中兵力進犯九江,加緊從江北向江南調遣兵力。
鹹豐四年十一月十八日(1855年1月6日),塔齊布從上遊琵琶亭渡江,次日移駐九江南門外。8日,新任湖北按察使胡林翼也率黔勇二千趕到,分紮要隘。9日,羅澤南又從下遊白水港渡江。曾國藩又調副將王國才所部三千余人的預備隊。這時,敵軍圍攻九江的總兵力已達一萬五千人。
九江,北依長江,東北有老鹳塘、白水港,西南有甘棠湖,西有龍開河,地勢險要,易守難攻。
守將林啓容已在四周嚴密設防,東南尤爲堅固。鹹豐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月14日),塔齊布、胡林翼攻九江西門,被林啓容以數十門大炮擊退,傷亡較多。林啓容連夜修整壕溝,深寬各至三丈余,溝外又豎木柵。

陶佳・塔齊布
鹹豐四年十一月三十日(1月18日),敵軍發動全面進犯,塔齊布攻西門,羅澤南攻東門,胡林翼攻南門,王國才由北岸登陸攻九華門。守軍分路迎擊,傷斃湘軍二百余名,參將童添雲中炮喪命。
曾國藩投入全部精銳:“因城上槍炮木石交施,屢次搶登,不能得手。”
原擬輕取九江的狂妄計劃,開始實施就遭到挫折。
曾國藩以九江城防嚴整難犯,改取“舍堅而攻瑕”的方針,留塔齊布繼續圍攻九江,派羅澤南、胡林翼進駐梅家洲南八裏之盔山(今灰山),企圖先取梅家洲“立木城二座,高與城等,炮眼三層,周圍密排;營外術樁,竹簽廣布十余丈,較武昌、田家鎮更爲嚴密;掘壕數重,內安地雷,上用大木橫斜搭架,釘鐵蒺藜其上。”
鹹豐四年臘月初六日(1855年1月23日),敵軍分路向梅家洲進犯,太平軍沉著應戰,斃敵數百人。曾國藩“攻瑕”又遭到痛擊。
于是,曾國藩第三次調整主攻目標,決定采用“越寨攻敵”戰術,先取湖口,企圖憑借水師優勢,掃蕩鄱陽湖內太平軍水營,切斷外援,最後再奪取九江。

彭玉麟
早在鹹豐四年十一月十五日(1855年1月3日),李孟群、彭玉麟即率水師進抵湖口,分泊鄱陽湖口內外江面。
石達開鑒于水師敵強我弱的態勢,難于立即取勝,決定采用疲敵戰法。鹹豐四年十一月二十日(1855年1月8日)夜,太平軍從贛江上遊用小船百余號,或二三只一聯,或五只一聯,堆積柴草,實以硝藥,灌以膏油,分十余起,縱火下放,炮船隨之;兩隊出動千余人,高聲喊殺,兼放火箭火球,夾攻敵船。但火船被敵人用篙撐入中流,順水而下,未能燒毀敵船。太平軍又于湖口城下沙洲加建木柵,在江面橫系筏纜數道,阻止湘軍水師近泊攻城。
鹹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55年1月15日),敵水師來犯,被擊斃百余人。此後,太平軍每夜以陸軍千余,在岸上用火箭火球抛擲敵船,大呼驚營,使敵軍徹夜戒嚴,不得安枕。
太平軍還在鄱陽湖口江面設置木廨數座,四周環以木城,中立望樓。木廨上安設炮位,與兩岸守軍相犄角,嚴密封鎖湖口,多次擊退湘軍水師的進犯。
鹹豐四年臘月初六日(1855年1月23日),湘軍水師乘陸師進犯梅家洲之機,又複來犯,炮中簰上火藥箱,巨簰被燃過半,但未燒之一面,守軍仍開炮不絕;望樓上的守軍更是屹立不動,直至全簰燃盡,望樓傾倒,才自投卻烈焰,或從簰底泅水而出。一場血戰,湘軍雖然燃燒了巨簰,仍然不能拿下湖口。
湖口之戰石達開、羅大綱迅速行動,連夜下令將大船鑿沉鄱陽湖口,實以砂石,僅西岸留一隘口,攔以篾纜沖入,太平軍民船三百余號,戰船三十余號被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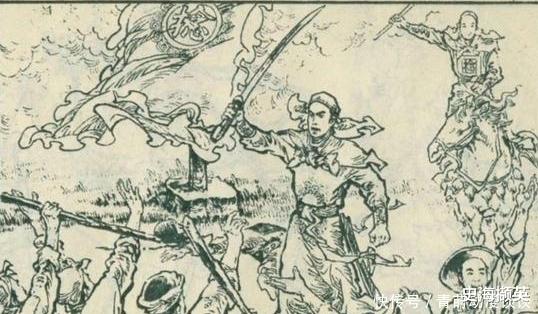
鹹豐四年臘月十二日(1855年1月29日),敵水師營官蕭捷三等率長龍、舢板一百二十余號,載兵二千,配合陸軍又沖入湖內,太平軍損失戰船數十號。
蕭捷雲屢勝而驕,不慮歸路,深入姑塘以上,想乘機打開“通江西饷道”。迨其回駛湖口時,太平軍已用船只搭起兩道浮橋,連結壘卡,將隘口堵塞,並以火力封鎖入口,使敵船不得再出。
至是湘軍水師遂被分割爲外江、內湖兩支:在外江者均爲長龍、快蟹等笨重戰船,運棹不靈,無舢板協助,“如鳥去翼,如蟲去足”,難于獨立作戰。
石達開立即瞄准戰機,即于當晚遣小船數十只,圍攻泊于長江內的湘軍大船,並用小劃三、四十號沖入敵營,火燒敵船,兩岸以陸軍數千,紛擲火箭噴筒,呼聲震天,焚敵大船九只,小船數只,雜色座船三十余只,敵水師敗退九江附近江面。
太平軍自嶽州退卻以來,取得了第一次重大勝利。
九江——湖口決戰在湖口大捷的同一天,江北秦日綱、韋俊、陳玉成等率軍自宿松西進,擊潰湖北清軍,收複黃梅。鹹豐四年臘月十六日(1855年2月2日),羅大綱遣隊自梅家洲渡江再占小池口,曾國藩因“水師既陷于內湖,陸軍複挫于小池口”,急調胡林翼、羅澤南二部,由湖口回攻九江,駐于南岸官牌夾。

曾國藩投湖
石達開決定進一步殲擊湘軍水師,令羅大綱于鹹豐四年臘月二十五日(1855年2月11日)渡江增援小池口。當夜三更,林啓容自九江,羅大綱自小池口,各派小劃數十只潛襲湘軍師船,乘黑夜無光,以噴筒火箭猛燒敵船,敵船除被焚外,余皆紛紛上逃,當即俘獲曾國藩座船,擊斃其管駕官劉盛槐、李子成、監印官潘兆奎等。曾國藩因事先乘小船遁入羅澤南陸營,羞憤欲尋死,被羅澤南等勸止。
太平軍湖口、九江連次大捷,湘軍外江水師頓成瓦解之勢,曾國藩的水上優勢趨于消失,輕取九江,直搗金陵的美夢遂告破滅。西征戰局爲之劇變,自湘潭失利以來,太平軍屢遭失利,節節退卻,陷入被動危急的困境,如今出現勝利的轉變。
石達開臨危受命,面臨強敵,冷靜謹慎地統籌九江——湖口決戰,秦日綱、羅大綱、韋俊、林啓容、陳玉成等骁將由翼王統一指揮,迅速縮短戰線,集中兵力,分據南北沿岸要塞,依恃廣闊的戰略後方,采取積極防禦戰略,以阻滯湘軍攻勢,並相機襲擾出擊,以疲憊敵人,使曾國藩在九江、梅家洲、湖口屢遭打擊。同時,石達開善于分析地形敵情,捕捉戰術性戰機,以迅猛果決的行動分割湘軍水師,進而繼續進攻,終于重創湘軍水師,開創了新的戰局。

再看湘軍,雖然獲得節節勝利,卻預伏著種種危機:擄獲甚多,“飽則思飏”,屢獲勝利,驕傲輕敵;長驅疾進,離後方基地越來越遠,運輸補給日益困難。
氣勢洶洶的表象掩蓋著虛弱的實體。湘軍在曆次戰役中傷亡沉重,精兵損失較大,經不起太平軍據城阻擊和日夜攻擾,其主要優勢惟恃水師,當兩次失敗後,外江水師瓦解,內湖水師沒有作用,陸師勢成強弩之末,太平軍反攻時機到來了。
三克武昌石達開看准清軍的第一線兵力全恃湘軍征戰,而後方卻是湖北綠營,腹地十分空虛。現在湘軍失去進攻能力,但曾國藩不肯輕離九江。
乘虛進攻湖北腹地是太平軍最佳戰略選擇。
于是,翼王令林啓容在九江牽制湘軍,而以秦日綱兵團向湖北發動大規模戰略反攻,以發展西征有利戰局。
鹹豐四年除夕(1855年2月16日),湖廣總督楊霈統兵勇五千余人駐守廣濟,正置酒歡飲,不料秦日綱兵團突至。清軍不戰而潰,楊霈逃至德安府(今安陸縣)。秦日綱、陳玉成乘機自黃梅率部西進,羅大綱亦遣軍三千,自小池口沿江西上,與秦日綱呼應。

太平軍先後收複廣濟、蕲水、黃州,鹹豐五年正月初七(1855年2月23日),第四次占領漢口、漢陽。
韋俊率部自田家鎮渡江,鹹豐五年正月初九(2月25日)進占興國,不久進占通山、崇陽、鹹甯,與秦日綱會攻武昌。此時,羅大綱經江西饒州,折回皖南。
湘軍水師自遭太平軍打擊之後,鹹豐五年正月初四(1855年2月20日)又遭風暴撞損,沉船二十二只,毀壞二十一只,曾國藩令彭玉麟撤往武漢,“名爲速剿上犯之賊,實則修整已壞之船。”
當時,湘軍已被分割爲五處:水師之一部開赴武漢休整,一部困在鄱陽湖內,陸師塔齊布部五千人留駐九江外圍,准備繼續攻城。李元度部三千人留駐湖口外圍,羅澤南部三千人往援贛東。此外,胡林翼、王國才率五千余人,回援武昌。
湘軍兵力分散,已被迫由進攻轉向防禦,在江西、湖北苦苦掙紮。
自鹹豐五年二月初四(1855年3月21日)起,秦日綱、陳玉成開始圍攻武昌。
新任湖北巡撫陶思培困守省城,僅只二千名兵勇守禦。清廷急速調兵增援,數日內,城外援兵已達萬人。鹹豐五年二月十七日(1855年4月3日),秦日綱、韋俊等會攻武昌。

城內敵軍一見黃旗,紛紛缒城逃跑,“外兵亦走。水兵固不任城守事,省城潰,僅自保而已。”太平軍迅速直趨城下,“用缒城繩引而上”,第三次勝利地占領武昌。擊斃湖北巡撫陶思培、武昌知府多山等文武官兵。
胡林翼的湖北湘軍鹹豐五年三月初三(1855年4月18日),清廷以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撫,李孟群爲湖北按察使。時胡林翼統湖北清軍,“屯金口,倚水師自保”,並“增募二千六百人,合王國才等軍,號六千。”至此,湖北湘軍始成羽翼,加緊擴軍訓練,准備同機反撲武昌。
從5月中旬開始,胡林翼即不斷對武昌、漢陽發動進犯,均被守軍擊退。
鹹豐五年二十六日(1855年6月10日),胡林翼又督四千余人分三路反撲武昌白沙洲、江堤、八步街等處。與此同時,王國才反撲漢陽西門外營壘,彭玉麟以水師協攻兩岸。太平軍雖略有損失,仍擊退了敵人的進犯。
當時,秦日綱等悉敵軍水陸師多在武昌、漢陽附近,後路紙坊、金口防兵單薄,乃由武昌潛師夜出,于鹹豐五年五月初十(1855年6月23日)晨,擊潰紙坊敵軍,直攻金口。
由于胡林翼已有准備,雖經多次進攻,均未得手。最後,又由紙坊退回武昌。其後,雙方在武漢附近,頻繁交戰,互有傷亡。

韋俊
鹹豐五年七月二十六日(1855年9月7日),韋俊自武昌出兵,會合自江西義甯州撤退將士,以及通城、崇陽等地的太平軍,于鹹豐五年八月初二日(1855年9月12日)攻占金口,擊潰湘軍陸師,並打敗登陸的水勇,李孟群敗退新堤(今洪湖縣)、六溪口等處。
胡林翼亦于鹹豐五年初四日(1855年9月14日)遁至蔡嶺,再遁往奢山(漢陽西南)。鹹豐五年初八日(1855年9月18日),太平軍連續進攻,自漢陽分兵圍取奢山,並以數千人抄後,湘軍不戰大潰,胡林翼羞憤之至,索馬欲陷陣,遇鮑超炮船救出,與王國才敗竄新堤。可惜,太平軍沒有乘勝追擊,使胡林翼得以死灰複燃,成爲日後威脅太平軍的又一勁敵。
石達開經營江西的原因原在鹹豐五年(1855年)11月初,石達開發動崇陽壕頭堡戰役時,曾與韋俊約定分路攻取湖南,韋俊由平樓峒攻嶽州;石達開則由崇陽、通城進攻平江,抄襲湘軍老巢。
但是,不久就改變了原來的攻湘計劃,除分遣四千人西援韋俊以外,于鹹豐五年十月十五日(1855年11月24日)親率主力一萬多人,自湖北通城突入江西,從而開始了在江西的勝利進軍。
是時,曾國藩妄圖力保江西,窺伺九江,以攻爲守。
石達開于鹹豐五年(1855年)11月初自安慶進抵鄂南前線,在壕頭堡取得殲敵一千余人的首戰勝利。但同時,從武昌南進的韋俊一軍,卻在湘鄂交界的平樓峒,連遭二次敗仗,先後損失三千余人。石達開鑒于韋俊的攻勢受到挫折,因而感到在鄂南或武昌周圍與敵人決戰,勝利把握不大。遂采取避實擊虛的戰略,甩開敵軍主力,攻敵之所必救,以調動敵人馳援以保衛湖北基地。

根據實際情況,是進軍湖南,還是進軍江西,究竟哪裏比較合適?
湖南是湘軍老巢,如果向這裏進軍,勢必給湘軍以極大的打擊。但是,當時湘鄂邊界敵人防禦力量比較雄厚;同時,湖南遍設團勇、練勇,僅團勇一項“頃刻可集數萬之衆”。
如果是孤軍深入湖南,不僅不易通過敵人的嚴密防線,而且敵人也要作拼死的頑抗,這樣可能重蹈鹹豐四年(1854年)的覆轍。
太平軍在江西有較好的活動基礎,重兵控扼九江、湖口,並活動于鄱陽湖東西兩岸。這些對于石達開經略江西的太平軍,將提供一個極有利的條件。
其次,江西有較好的群衆基礎。
原來,廣東天地會起義部隊,已由湖南茶陵州進入江西,于鹹豐三年九月二十一日(1853年10月23日)擊敗清軍,占領江西永新縣。旋即退出,先後占領安福、分宜、萬載,于十一月初六日(12月6日)向新昌(今宜豐)挺進;同時,另股天地會也于十月二十九日(11月29日)由湖南入贛,占領永甯縣(今甯岡)。

另外,江西本地群衆也不斷掀起反抗風暴。鹹豐三年(1853年)2月,在武甯有周逢春領導的起義,6月,在龍泉有劉通義領導的起義,在上猶有胡志荛領導的起義;7月在泰和有鄒思隆領導的起義,8月在興國有黃蠟梨領導的起義;9月在南康有朱士華領導的起義;鹹豐五年(1855年)夏,在安遠有李白古領導的起義,同年11月,鉛山湖坊的起義群衆曾殺死巡檢鄭承先。這些反清鬥爭對于太平軍入贛將是有力的支援和配合。
第三,這裏地處長江中遊,毗連六省,戰略地位異常重要。向這裏進軍,不僅可以擴大天國版圖,把蘇皖鄂贛連成一片,而且還可以直接威脅躲在南昌的曾國藩,迫使他撤退九江和武昌的圍師。如是,九江之圍可以不戰自解,武昌的壓力也會因此的減輕。應當說這是變被動爲主動的正確戰略決策。
同時,這裏敵人力量也比較薄弱,曾國藩系統的湘湖軍陸師只有李元度部三千人,周鳳山部四千人,水師只有彭玉麟統率的八營約四千人,總共只有萬余人,並且被膠著在九江湖口外圍與鄱陽湖內的幾個據點。
江西本省系統的防兵,在南昌只有二千余名。全省募勇一萬五六千名,共分二三十隊,或數百人一隊,或百余人一隊,各不相統屬。
比起湖南,江西清軍力量相對虛弱,難以阻擋太平軍的攻勢。經過權衡後,石達開決定率軍突入江西。
石達開開辟江西基地的高明之處石達開率軍突入江西後,十月十五日(11月24日)在義甯州境內岸鄉小鬥嶺下,以詐敗、設伏的戰術,擊潰了敵軍,陣斬清軍總兵劉開泰等人。十一月初一日(12月9日),石達開再敗扼守八疊嶺的團勇,隨即占領新昌。同時,分兵攻克上高。此時,石達開會合由周培春等天地會義軍約數萬人,勢力大增。12月中旬,石達開分兵三路,同時向瑞州(今高安)、臨江和新余進軍。

石達開
石達開率領的太平軍,于鹹豐五年(1855年)11月下旬自湖北突入江西,到鹹豐六年(1856年)4月,前後不到半年時間,連克七府四十七縣,加上原來已占有的九江府(包括附郭縣德化)、湖口、彭澤,總共爲八府五十個縣。但是其中有些縣,如安仁、萬年、余幹、樂平、德興、浮梁,只是路過而已,並未據守。還有,南豐只占一日,萍鄉已于鹹豐六年二月十二日(1856年3月18日)先陷。故至4日時,太平軍在江西實際據守的府縣是八府四十二縣。當時西征軍中流傳這樣一首歌謠:“破了鑼,倒了塔,殺了馬,飛了鳳,徒留一個人也無用。”
在石達開正確戰略指揮下,西征戰局發展迅速,湘軍連遭挫敗,悍將調零,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他在江西的慘敗爲軍興以來各省所未見。
石達開在江西勝利的原因有二:一是廣東天地會友軍和江西起義群衆的有力配合。石達開入江西時的兵力只有一萬多人,要占領全省五十多個州縣,本來是不可能的。但是石達開正確爭取了天地會和起義群衆的合作,從而妥善解決了占領區擴大和兵力不足的矛盾。
據曾國藩估計,在鹹豐六年(1856年)3月下旬,即石達開離開江西之前,江西太平軍已發展到十萬人(包括婦孺在內)。在石達開帶走二三萬人之後,留守江西的還有太平軍老戰士一萬人,天地會軍約三萬人,新參軍的江西群衆約三萬人,總共還有七萬人。
由于太平軍的迅速壯大,根本改變了敵我力量對比的形勢,因而得以擊敗湘軍,掃蕩江西綠營,出現了“贛水以西,望風瓦解”的大好形勢。

石達開
二是石達開具有傑出的軍事才幹。他善于“審時度勢”,利用敵人的弱點和錯誤,作出正確的戰略決策。
在援鄂途中,當機決斷,避開湘軍主力,突入防禦比較薄弱的江西。在經略江西戰略上,翼王沒有立刻急于攻取南昌,而是鑒于南昌的地勢“三面濱河”,敵人又擁有“戰船二百余艘”,正在贛江、撫河來回巡弋,而太平軍沒有水師,無法合圍省城。
于是石達開充分發揮陸師優勢,大踏步地向腹地進軍,采取“先旁收郡縣”,“落其枝葉,以撼其根本”的戰略。
後來曾國藩也看出了這個戰略的意圖,是使清軍“疆土日狹,饷源日竭,省會成坐因之勢。”迨條件成熟後,南昌便不攻自破。左宗棠驚呼:“自章門數十裏外,西抵吾鄉,北抵浔,皆賊蹤也。”
是時,龜縮南昌的曾國藩與湘軍的聯系已基本被切斷,募人以蠟丸隱語偷關逾卡相回答,又往往爲太平軍所截獲。因此,曾國藩不得不發出“道途以梗,呼救無從,中宵念此,魂夢屢驚”的哀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