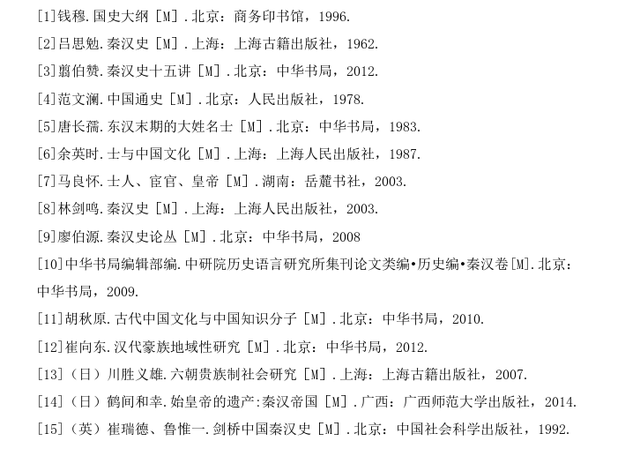文|卡門的提琴
編輯|卡門的提琴
東漢末期,一共發生發生了兩起黨锢之禍,慘絕人寰的政治屠殺,上演了一出人間悲劇。
當時,宦官與士大夫之間的矛盾已凝結成燃眉之急,然而,黨人集團並未就此得逞。
相反,黨锢之禍徹底動搖了東漢王朝的根基,隨後爆發的繼位戰爭與起義戰爭終于拉開了王朝覆滅的序幕。
幾百年的昔日盛世就此化爲烏有,一切都要從頭再來。
那麽,黨锢之禍的起因是什麽?又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漢末社會矛盾加劇
漢末社會矛盾加劇東漢王朝步入和帝時期,便開啓了一段令人扼腕歎息的黑暗歲月。
那個時候,宦官和外戚兩大集團開始在朝政上彼此角力把持權力,他們借助親疏關系竊取國家權力,在朝野之間劃分勢力範圍,擴張自身利益。
這種行爲無疑是對正統王室權威的公然挑戰,在這些人手中,東漢王朝逐漸淪爲了一盤遊戲棋局,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角逐、勾心鬥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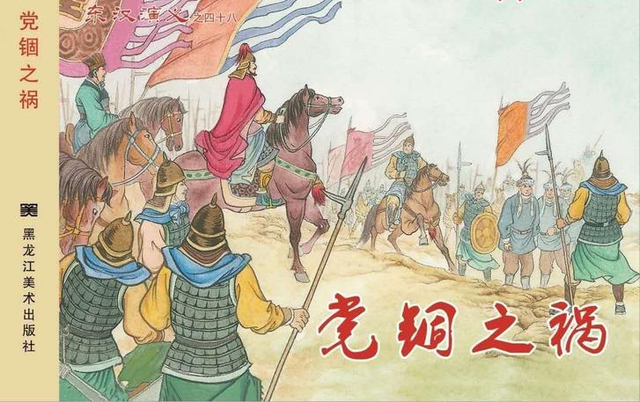
朝政日漸黑暗腐朽,民不聊生,普通老百姓在他們的欺壓掠奪下,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水深火熱之中。
到東漢末的桓帝、靈帝時期,宦官的權勢達到頂峰,他們操縱官員的選拔,任人唯親,排斥異己。
在個人生活方面,他們窮奢極欲、毫無節制。

宦官徐璜的侄兒出任下邳令時,竟然公器私用,濫用職權,原因竟是出于一股旖旎的私欲——他熱衷于追求故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兒芳澤,但是卻遭到了拒絕。
他竟然以職務之便,公報私仇地窮凶極惡,對李家人施加了種種非法手段和迫害,“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
宦官曹節的兄弟破石做越騎校尉時,強奪士兵的妻子,最後逼的其妻子自殺。

宦官子弟的此類劣行不可勝數,國家權力掌握在這樣的人手裏,其政治的黑暗程度可見一斑。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百姓生活的極端貧困。

延熹六年,時任光祿勳的陳蕃上書桓帝稱當時社會有“三空”,即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延熹八年,劉瑜上書言事稱:“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奸情赇賂,皆爲吏餌。民愁郁結,起入賊黨,官辄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

甚至在司隸、豫州這樣的經濟發達地區,也出現了“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這種人間慘劇。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政治的黑暗腐朽,在東漢末年,種種天災也是頻頻發生。

僅《後漢書·桓帝紀》中記載,從桓帝即位的本初元年(146年)至黨锢之禍爆發前的延熹九年(166年)的20年時間裏,共發生水災8次,地震12次,旱災1次,疫病3次,蟲災3次。
平均每年都至少發生一次自然災害,而且受災面積大,發生的地點又多是經濟發達、人口稠密的地方,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加嚴重。
除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周邊少數民族的入侵和反叛,也加劇了東漢朝廷的財政困難。

據《後漢書·桓帝紀》記載,同樣是在桓帝即位之時到黨锢之禍爆發的20年間,少數民族入侵達31次之多,遍布整個東漢的邊境線。
與此同時還有遍布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14起。
這些都使得東漢政權的財政愈加困難。

爲了平息叛亂和起義,抵禦少數民族入侵,東漢政府甚至減少官員的俸祿來籌措軍資。
官員俸祿的減少,必然導致那些本身就貪汙腐敗的官員,更加殘酷的剝削底層人民,以維持他們奢侈腐朽的生活。
吏治腐敗、天災不斷,加上少數民族的入侵和人民的起義,都使得東漢末年的社會矛盾不斷加劇,清流官員將這些矛盾的根源都指向了“手握王爵,口含天憲”的宦官階層,雙方的對立和矛盾愈加尖銳,一場鬥爭在所難免。
 權力的爭奪
權力的爭奪到了東漢,由于開國之主漢光武帝本身就喜歡儒術,于是官員仕途是否通暢就和是否習儒通經更加密不可分。
在地方上,習儒通經也成爲了豪族與權力結合的重要途徑。

東漢後期,由于宦官把持朝政,企圖經過通明經術走入政壇的士人遭到排擠,如濟北相滕延因得罪宦官侯覽、段珪而被免官。
廷尉馮绲殺了宦官單超的弟弟,導致“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绲,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輸左校。”
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因爲打擊宦官及其黨羽而被捕死于監獄。

據統計,東漢光武帝、明帝時期,公卿95人,儒者出身36人,占38.9%,自章帝至桓帝,公卿209人,儒者出身90人,占43%。而到了靈帝和獻帝時,儒者在官員中的占比下降到了35.2%和26%。
由于整個東漢時期士人階層是在不斷的擴大,而後期在官員中所占比例又在不斷縮小,其受到排擠的程度可見一斑。

在黨锢之禍發生後,爲了進一步打擊太學生,控制士人的入仕途徑,昏庸無能的漢靈帝在宦官的慫恿下,在太學之外又開設了鴻都門學,來培養擁護自己和宦官集團的知識分子,士人受到進一步的排擠。
士人階層雖有權力野心,但面對皇室統治不得不隱藏銳氣,只有當朝政腐敗、君主荒唐,皇權被宦官外戚把持時,他們才能借機東山再起。

表面上,士人們自诩爲忠良谏言、國家脊梁。
但實則,他們也懷揣擴張權勢的企圖,只不過,與那些公然竊國作亂的宦官外戚不同,士人階層更加善于隱藏野心,伺機而動。

然而,黨人與宦官的鬥爭,本質上是國家最高統治權力之爭。憑借家族優勢攫取政治權力,取代宦官集團,這就是黨人鬥爭的目的。
在王權支配下的中國古代社會,任何威脅或是侵犯到皇帝權力的行爲都是王權絕對不能接受的。
古代中國曆朝曆代的君主基本都會采取各種手段來加強和穩固中央集權,漢代同樣也是如此。

從漢武帝限制丞相權力設置“內朝”、頒布“推恩令”、獨尊儒術到光武帝擴大尚書台權力,都是爲了加強中央集權,使朝中大權盡可能地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
然而隨著東漢時期地方豪族大姓的發展,他們的勢力越來越大,逐步脫離了中央的控制。

清議之風掀起之後,黨人憑借其名望,在地方上幾乎擁有了獨立于甚至超過國家司法體系的權力。
黨锢之禍的導火索——“張成事件”,便是黨人的領袖之一李膺在遇到朝廷大赦的政令後,無視法律,依然處死了張成之子。
此外還有成瑨、岑晊遇赦不赦殺掉勾結宦官的“南陽大滑”張汎,太原劉瓆擅自殺掉爲害一方的宦官趙津。
這些事件亦足以說明黨人集團所擁有的巨大權力。

同時,清議運動使得當朝權貴“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第一次黨锢之禍後,李膺的個人聲譽也是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甚至在社會上出現了“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的現象。
這也反映出了黨人的聲望所影響到的已經不僅僅是宦官集團,其背後的皇權也受到了威脅。
 黨锢之禍的影響
黨锢之禍的影響第一次黨锢之禍前後僅持續了一年就結束,對整個東漢政權造成的影響不是很大。
第二次黨锢之禍持續了近二十年,直到到黃巾起義爆發後,漢靈帝才宣布解除黨锢,大赦黨人。
第二次黨锢之禍所導致的直接後果是“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

黨人集團的本意並非是爲了推翻東漢政權,他們是想通過政治改良的手段以挽救這個政權。
可是第二次黨锢之禍對他們長達二十年的禁锢,使他們無法對這個政權采取任何挽救措施,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它迅速衰敗到無法挽救的地步。

後世史學家也認爲,第二次黨锢之禍持續太久,等到解除黨锢的時候,東漢政權已然無藥可救。
林劍鳴先生也認爲:在黃巾起義的時候,東漢的統治者才想到解除黨锢以抗拒人民的打擊,這對于挽救東漢的滅亡,已經無濟于事了。

在第二次黨锢之禍期間,宦官集團一直掌握著中央大權,權勢與日俱增,史書稱其:“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賤,爲人蠹害。”
即使宦官們的實際權力被剝奪,他們依舊操縱著皇帝,讓皇帝像個傀儡般任憑擺布。
爲了不讓皇帝看見他們居住的奢華府邸,欺騙靈帝說:“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靈帝果然“自是不敢複升台榭。”

中平六年(189年),漢靈帝病死,少帝劉辨繼位。
外戚何進擔任大將軍,執掌朝政大權,並圖謀誅除擅權的宦官張讓、趙忠等人。
但經曆過第二次黨锢之禍的宦官,已經學到了該如何應對這種局勢,他們又一次搶先行動,引誘何進入後宮,後將其殺害。

智謀不足固然是外戚失敗的一個原因,但卻並不是唯一的原因。
尤其是何進掌權時,宦官勢力龐大,但士大夫階層,卻剛剛經過第二次黨锢之禍長達二十年的打擊,大部分已經無力再支持何進與宦官鬥爭。
少數有能力者,或是屍位素餐,不願卷入新的紛爭;或是另有所圖,無心忠于漢室。

王夫之將這一局勢分析爲:“內懷奪柄之心,外無正人之助”
宦官集團長期的把持朝政、胡作非爲,必然引起新一批官僚的不滿。
在何進被宦官謀殺後,握有軍權的一方豪傑——袁紹站了出來。
袁紹在第二次黨锢之禍時就站在黨人一方,曾幫助何颙保全了衆多黨人。

第一次黨锢之禍後,袁紹目睹了陳蕃、窦武失敗的整個過程,第二次黨锢之禍後,又目睹了何進謀誅宦官失敗。
袁紹吸取了黨人失敗的經驗和教訓,意識到僅憑清議和輿論是無法與宦官對抗的,要徹底鏟除宦官必須依靠暴力。
他在行動時也沒有像窦武、何進一樣猶豫不決。在何進被殺,宮廷一片混亂之際,袁紹果斷領兵打擊宦官,從和帝時開始掌權的官宦集團,被徹底鏟除。
 總結
總結黨锢之禍是東漢正直士大夫爲了挽救朝政而與腐朽的宦官勢力産生矛盾,最終士大夫被宦官殘酷打壓的兩次次政治鬥爭。

黨锢之禍前後共發生兩次,兩次黨锢之間,以窦武、陳蕃爲首的黨人集團短暫掌權,然而窦武、陳蕃勢力與宦官的較量終以慘敗收場。
兩次黨锢期間,大量黨人遇害,整個士大夫階層受到殘酷打擊,然而,兩次黨锢之禍並非是簡單的兩次同類型事件的重複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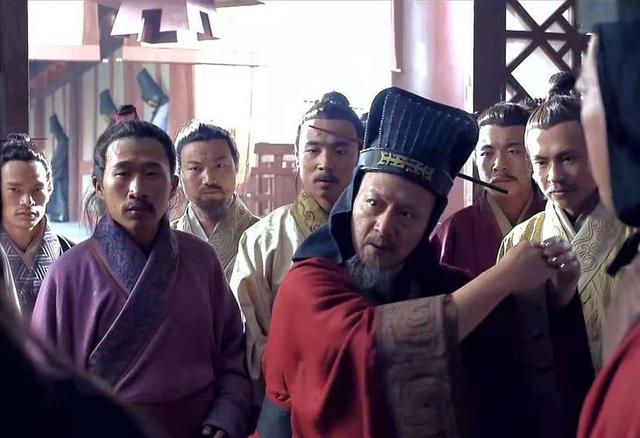
它們在興起的原因上有相同點和不同點,在牽涉到的人群上也有區別,所帶來的影響更是不盡相同。
總體上講,第二次黨锢之禍可以說是第一次黨锢之禍的蔓延、擴大和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