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會有很多的身份,比如王維,他是大唐的官員,是一個畫家,是一個作家,是一個音樂家,是一個虔誠的佛徒,更是一個凡人。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王維與自然,那是充滿禅意與畫意的自然世界。
“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雲。”王維與朋友,那是深情真摯的情誼。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維與使命,那是滿滿慷慨悲壯之情。
“白雲回望合,青霭入看無。”王維與名利,那是如浮雲般淡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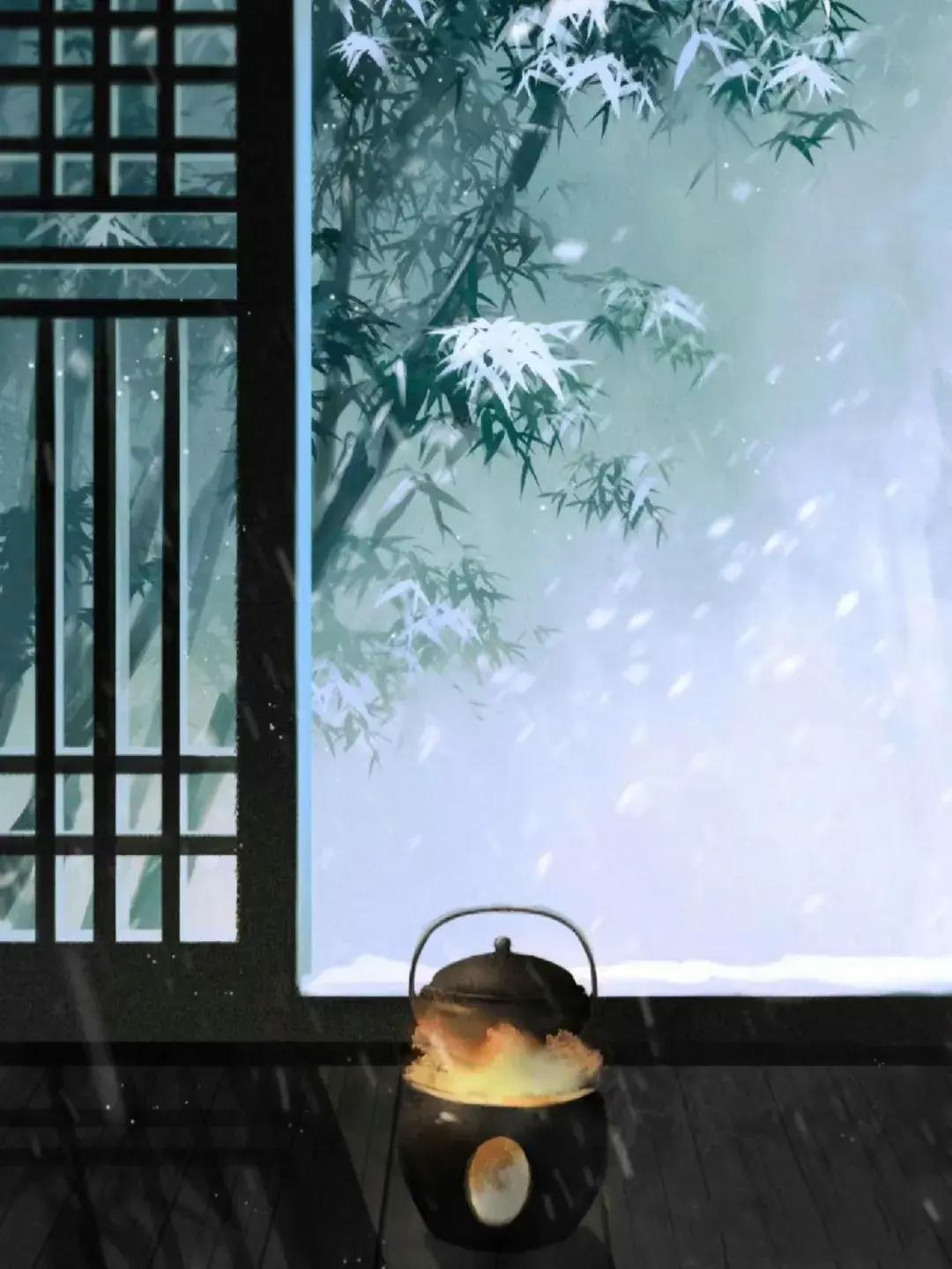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終南別業》
終南山下的辋川山莊,原來是宋之問的,後來王維買下的本意,是爲了給信奉佛教的母親提供一個清淨之地,安心修行。
後來朝堂變幻,王維逐漸起了歸隱之心,開始不斷遊離在廟堂與江湖之間。
辋川別業就成了王維追尋心靈安甯的重要場所,他的很多作品都與辋川別業有關。這個空間不單是一處宅院,更是一個精神上的空間。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王維這個時候已經到了人生的後期。王維的官做得很大,做尚書右丞(四品)他說人到中年,開始試圖尋求“道”。
一個人想要求道,試圖放下,大概是看透了塵世的煩雜。(或許也有不得意的成分在裏面,希望在求道的過程中獲得一些安慰。)
有時候興起,就一個人出門走走。自由自在。不設置終點,就這麽無牽無挂、不管不顧地走下去。
路在心裏,可以一直走下去。信步悠閑漫步于山間,靜靜體味大自然造化中所蘊含的佛家真谛。
累了坐下來,看天上的浮雲,看看地下的淙淙流水。
生命本身其實沒有什麽終點,它只是一個過程。它是每時每刻,是無數個“現在”的集合。它可以是水,它也可以是雲。它可以是行,它也可以是坐。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許多人,許多事,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偶然碰到,是我們的幸運。王維偶然遇到一個砍柴的老人,結果發現兩個人還挺聊得來。
他和這個老人能聊些什麽呢?
大抵是陶淵明說:“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孟浩然說:“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他們會聊莊稼長得怎麽樣了。對生活在田間的人來說,這可是頭等大事。
就這麽聊啊聊啊,一直聊到天黑也沒想到要回家。估計他都忘了還有回家這回事。
當時間不再起作用的時候,此刻就是永恒。當心裏不再記挂著彼岸的時候,此岸就是彼岸。這種超然物外的心境與閑逸恬淡的情懷,我們所不能達到的高度。
卞之琳有詩雲:“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王維大概想著:進可攻,退可守,官嘛,做與不做都不打緊的,其實這樣不也挺好嘛。

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饷東菑。
漠漠水田飛白鹭,陰陰夏木啭黃鹂。
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
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唐·王維《積雨辋川莊作》
晚年的王維不再糾結廟堂與江湖,徹底歸隱山林,真正的回到自然。
下過一場雨,草木都被打濕了。農村要燒火做飯,打濕的柴火不容易點燃,所以是“煙火遲”。飯做好了之後,送到田間地頭給這些幹農活兒的人吃。
水田一眼望不到邊,綠油油的莊稼上飛起一行白鹭,夏日濃萌,傳來黃鹂婉轉的啼叫聲,這是很漂亮的田園景象。
前一句寫畫面,後一句寫聲音。
王維說自己在山裏修佛,吃的齋飯很清淡,在自然裏感悟生命,什麽叫“朝槿”呢?朝槿就是木槿花,它的花期很短,早上開,傍晚就落了。
其實人生又何嘗不是這樣呢?王維在木槿花,花開花落裏慢慢了悟到生命的無常。
這裏的村夫野老已經和王維這位官人詩人沒有了隔閡。
“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最後這一句裏有兩個典故。

先說第一個。楊朱有一次碰到了老子。老子對他說:本來以爲你還有得教,現在看來,你這個人徹底沒救了。
楊朱一聽,嚇壞了,一句話也不敢說,乖乖地跟著老子到了旅店。
等到了旅店,楊朱恭恭敬敬地跪在老子面前請教。
老子說:你這個人這麽傲慢,誰願意和你待在一起呢?
楊朱一聽立馬就懂了。
楊朱剛來到這間客店的時候,大家對他非常客氣,有人給他端水,有人給他遞毛巾,有人給他讓座位。
等到楊朱要離開這間客店的時候,沒人給他端茶倒水了,大家都和他爭搶座位。
楊朱放下了自己的傲慢,大家也就不拿他當外人了。自家人是不必客氣的。
王維說“野老與人爭席罷”,說的是他自己,回到人群裏,村裏的人也和他爭搶座位。他成了他們中的一員。這其實才是修行。
真正的修行,其實是把自己放回人間。
王維還用了鷗鹭忘機的典故。
有一個小孩,很有靈性,每次他去海邊,那些海鷗們都會落到他身邊。有一次他父親和他說:你既然和海鷗關系這麽好,不如你去抓兩只海鷗回來。小男孩就去了。可是當他到了海邊,他發現這些海鷗只在他頭上盤旋,卻再也不落下來了。
人有了機心,就和自然裏的萬物有了隔膜。
王維的意思是,當自己放下塵世的算計,就能重新感知到自然,重新成爲自然的一部分了。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
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唐·王維《辛夷塢》
辛夷塢就是在辋川山莊這個地方選一別處種上了辛夷花。
辛夷花不同于梅花、桃花之類。它的花苞打在每一根枝條的最末端上,形如毛筆。辛夷含苞待放時,很象荷花箭,花瓣的顔色也近似荷花。
王維應該除了是個畫家,還有一個身份,兼職攝影師。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辛夷花開在枝頭,有的還沒有完全開,只是一個個花骨朵。
所以王維並沒有見到花完全盛開的樣子,當然,他也不會在同一時刻看到花紛紛落下。
當春天來到人間,辛夷在生命力的催動下,欣欣然地綻開神秘的蓓蕾,是那樣燦爛,好似雲蒸霞蔚,顯示著一派春光。
王維筆鋒一轉,將辛夷花置于一個山深人寂的環境之中,寫它開時即熱烈地開放,使山野一片火紅,落時則毫無惋惜地謝落,令人想象花瓣如缤紛紅雨灑落深澗。
它自開自敗,順應著自然的本性,它自滿自足,無人欣賞,也不企求有人欣賞。就如張九齡筆下的香草桂花,有人也芬芳,無人也芬芳。
這首詩在說什麽呢?
王維其實在說,一個生命的降臨和消逝,並不依賴于外界的觀看。
一朵花並不會因爲你的到來而盛開,也不會因爲你的離開而落下。
每一個生命都是孤獨的,但每一個生命也都是自足的。

獨坐幽篁裏,彈琴複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唐·王維《竹裏館》
王維在他的大別墅裏順著山水修葺了一個落角,裏面種了很多竹子,命名爲《竹裏館》。
當你讀到他的這首詩的時候,瞬間你就會進入到了那意境當中,不能自撥。
坐在竹林深處彈琴的王維,就好像生長在山水間的辛夷花一樣。
王維抒寫自我情懷,選擇了彈琴與長嘯,則取其與所要表現的那一清幽澄淨的心境互爲表裏。
這一月夜幽林之景是如此空明澄淨,在其間彈琴長嘯之人是如此安閑自得,塵慮皆空,外景與內情是泯合無間、融爲一體的。
在這個清幽絕俗的情景中,詩人借助月下獨坐、彈琴長嘯的悠閑生活狀態,傳達出甯靜、淡泊的心情。詩中運用了擬人的修辭方法,把傾灑著銀輝的一輪明月當成心心相印的知己朋友。
沒有人理解不打緊,不是還有天空中的一輪明月陪伴嗎?其實這樣也很滿足了,不是嗎?
裴迪有詩雲“來過竹裏館,日與道相親。出入唯山鳥,幽深無世人。”什麽意思呢?他說來過竹裏館的人都知道,每日出走在山間小道上,倍感親切。 山林中只有山鳥飛進飛出,幽深得看不見人。
還真別說,這個實景真如他所寫,但是境界他實在是寫不出來。

獨坐悲雙鬓,空堂欲二更。
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
白發終難變,黃金不可成。
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
——唐·王維《秋夜獨坐》
這首詩表達的內容並沒有什麽特別之處,無非是在晚上爲自已的老去感到悲傷,並且領悟到只有通過修佛參禅才能忘卻人間的煩惱。
這是一個秋天雨夜,更深人寂,詩人獨坐在空堂上,潛心默想。這情境仿佛就是佛徒坐禅,然而詩人卻是陷于人生的悲哀。他看到自己兩鬓花白,人一天天老了,不能長生;此夜又將二更,時光一點點消逝,無法挽留。
一個人就是這樣地在歲月無情流逝中走向老病去世。這冷酷的事實使他自覺無力而陷于深刻的悲哀。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他越發感到孤獨空虛,需要同情勉勵,啓發誘導。
然而除了詩人自己,堂上只有燈燭,屋外聽見雨聲。于是他從雨聲想到了山裏成熟的野果,好象看見它們正被秋雨摧落;從燈燭的一線光亮中得到啓發,注意到秋夜草野裏的鳴蟲也躲進堂屋來叫了。
詩人的沉思,從人生轉到草木昆蟲的生存,雖屬異類,卻獲同情,但更覺得悲哀,發現這無知的草木昆蟲同有知的人一樣,都在無情的時光、歲月的消逝中零落哀鳴。
詩人由此得到啓發誘導,自以爲覺悟了。

冬宵寒且永,夜漏宮中發。
草白霭繁霜,木衰澄清月。
麗服映頹顔,朱燈照華發。
漢家方尚少,顧影慚朝谒。
——唐·王維《冬夜抒懷》
此詩大約作于天寶元年(742年)前後。李林甫當政時,王維作爲張九齡起用之人,因而在政治上受到壓抑,眼見年華流逝,老之將至,卻依然位居人下,而那些投靠李林甫的年輕無行文人卻青雲直上,心中不勝感慨,而作此詩。
王維正是張九齡一手提攜上來的,隨著張九齡罷相,少了伯樂的賞識,再加上王維實在是不願與李林甫同流合汙,所以王維一度飽受排擠,心裏極度痛苦。
在一個冬夜,王維獨自面對著凝霜的草木和清冷的月光,從身體到心靈都彌漫著一種肅殺的氣氛。
他心中充滿了懷才不遇的苦悶和慚愧,這種感覺在他的錦繡華服與衰老的容顔、紅燭的鮮亮與白發的蒼老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他運用紅燭和白發的色彩對比,表現了自己在歲月蹉跎中未實現壯志的悲憤之情。這種畫面具有極強的感染力,讓人深感共鳴。
另一方面,華服與紅燭象征著生命的絢爛,而衰顔與白發則象征著生命的枯萎。這種鮮明的反差讓人深感震撼,引發人們對生命的無常和人生的意義的深思。
王維在朱燈前,看著自己的白發,想起了漢代顔驷不遇的典故,以此自比。他在抱膝燈前,顧影自憐,這種自憐的情緒讓他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了不遇之悲。
情感很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因爲色彩不僅帶來了生動的畫面,更引發了人們深入的思考和聯想。
如此孤燈白頭,王維在上一首詩裏“雨中山果落, 燈下草蟲鳴”以禅入詩:“白發終難變, 黃金不可成。”

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不妥,聯系立即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