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流媒體巨頭網飛(Netflix)制作的網劇《三體》自上線以來,雖然在歐美評論圈口碑尚可,在中文世界卻差評不斷。劇情的大幅刪改尤其引起了原著粉絲不滿。從播放數據上看,該劇開播四天後就登頂93個國家和地區的播放榜首,同時帶動了原著小說在亞馬遜平台上的銷量。但這種面目全非的“文化出海”是很多原著粉絲不願看到的。
網飛版《三體》進行“魔改”的原因不難理解,海外的付費用戶才是這部劇要抓住的有效流量,他們大多沒看過原著,所以必須以他們最容易進入的方式改編。但即便基于這個原因,原著中深邃的科學性與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注都被犧牲了,還是非常遺憾。不只因爲此前許多評論指出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差異,還有流媒體與傳統電影、電視劇制作邏輯的區別。
故事題材與傳播媒體是有適配性的。正如今年正值風口的互聯網短劇專爲豎屏而生,其選用最多的就是情節誇張、沖突強烈的霸總、逆襲故事。流媒體也有適合制作的題材,而史詩故事可能恰好在其適配區之外。這篇文章將以網飛版《三體》爲切口,嘗試分析那些和流媒體邏輯不兼容的題材類型。

撰文|海客
作爲中國科幻的扛鼎之作,劉慈欣的《三體》系列,不僅在國內有著非常多粉絲和讀者。在國外也有著十幾種語言的翻譯版本和百萬級別的銷量。包括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日本知名遊戲制作人小島秀夫等,也都是《三體》系列的書迷。可以說,《三體》系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中國流行文化産品的出海之旅。
《三體》原作的魅力,自然會讓人期待,在美國強大的電視劇制作工業體系之下,網飛版《三體》劇集能夠生動再現原作中那些奇妙的科幻設定、精巧的故事與結構,以及原作所表達的中式思想內核與美學表達。稍早之前上映的維倫紐瓦執導的電影《沙丘2》,也讓人們看到了經典科幻作品中的這些特質,是可以做到近乎完美的影視化再現的。
但是,與上線之前的期待不同,網飛版的《三體》劇集在播出之後,卻因爲對人物和情節的刪節改動,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大量的爭議與討論。日本知名遊戲制作人小島秀夫就在個人社交媒體表示:“我真的很希望人們讀一讀原著,對于原著粉絲來說,我可能會推薦騰訊版(《三體》電視劇)。”
那麽網飛版《三體》的改編,到底是基于什麽樣的創作理念,才會使得主創團隊要對原作進行如此大刀闊斧的改編呢?

網飛版《三體》劇照。
“短平快”網劇模式
遇到宏大史詩
雖然同爲經典科幻作品的影視化改編,但是維倫紐瓦的電影版《沙丘》系列和網飛版的《三體》劇集,卻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模式。
走進電影院看電影,對于電影觀衆來說,本身就是一件帶有唯一目的性的,具有儀式感的行爲。電影院沉浸式的觀影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隔絕了日常生活,從而可以保證觀衆在觀看電影的這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裏,注意力是集中在電影內容上的。在這個前提下,優秀的電影的創作者,是可以專注于電影內容的表達,而無須考慮怎樣去抓住觀衆的注意力的。
正因爲此,維倫紐瓦執導的《沙丘》可以用相對緩慢的節奏,去以畫面再現沙丘世界的完整風貌。而這種再現整個世界的宏大感,並不是電影的某一個片段所能體現的。因此,在觀看《沙丘》時,觀衆獲得的不是觀影過程中不斷被刺激的即時滿足,而是看完整部電影之後,完整的觀影體驗所帶來的滿足感。
對于電視劇來說,這種儀式感和目的性是不存在的。電視劇對于我們來說,是一件極其普通的日常活動。觀看電視劇的過程,與我們的日常生活之間,是沒有嚴格的邊界的。這就要求,相較于電影,電視劇要更加能夠抓住觀衆的注意力,更加強調即時的反饋與刺激。
對于傳統的在電視上播放的電視劇來說,唯一能夠保證的播放時間上的唯一性。傳統的美國電視劇,一般采取每周一集,固定時間播放的模式。對于想要觀看某個劇集的觀衆來說,幾乎唯一的觀看方式就是每周固定的那個時間在電視上觀看。
而到了流媒體時代,這種時間上的唯一性也已經不複存在了。流媒體時代電視、手機、平板一個賬號多設備無縫切換的觀看模式,以及隨時暫停,隨時回看的便利性,正在改變觀衆們的看劇模式。

網飛版《三體》劇照。
正如美國專欄作家洛裏·博格曼在《這是鳥!這是飛機!這是商業!》所寫的:她的孫子們從小就習慣了在網飛和亞馬遜金牌會員等流媒體平台。當這些孩子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觀看電視上播放的電視劇時,他們的注意力會時不時地被上廁所,吃東西之類的瑣事打斷。而當博格曼告訴孩子們,在電視上看劇,是沒有辦法暫停或者回看的時候,這些孩子露出了異常困惑的表情。
在這種情況下,觀衆的觀看方式更加的多樣化與碎片化。而頻繁暫停的碎片化觀看方式,會極大影響觀看的體驗和代入感。進而導致“暫停”發展成“棄劇”。因此,作爲制作方的各大流媒體平台,爲了抓住觀衆注意力,會更加強調劇集的即時反饋與刺激,力求讓觀衆一口氣不停歇地看完。
正因爲此,相較于之前那些在電視台播放的“傳統”美劇,網飛等流媒體平台制作的劇集,往往有著更快的敘事節奏,以及更多、更頻繁的內容爆點。例如,由美國有線電視頻道原創的,被譽爲“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電視劇之一”的《絕命毒師》,其節奏和故事展開,相較于網飛的絕大多數劇集,都要慢上很多。
但是,當這種講究“短平快”,追求即刻反饋與爆點的制作理念,遇到大部頭的經典作品改編的時候,就往往會出現問題。
以流量爲錨點的
制作邏輯
現在對于網飛版《三體》的正面和負面的評價,大多數也都是基于這種創作理念而來的。網飛版《三體》的正面評價,大多都在說,這是一部制作精良,節奏明快,可以輕松無門檻觀看的劇集。這些正是美國成熟的電視劇工業體系,以及流媒體平台制作理念的強項。
而負面評價,則往往會指出,網飛版《三體》對于原作人物,劇情以及科幻設定粗暴的扁平化、簡單化處理。實際上,這些對原作魔改的處理方式,同樣也來自于流媒體平台的制作理念。
對比騰訊版《三體》和網飛版《三體》的評價,就會發現,對于兩者的評價,恰好呈現出了某種“共轭的互補”。對于騰訊版《三體》,正面評價大多來自于劇集對于原作人物,情節和經典名場面的忠實還原,而負面評價則一般會指出節奏拖沓,涉及核心設定的部分稍顯晦澀等問題。
但是,實際上,騰訊版《三體》和網飛版《三體》在制作上采取的這兩種完全相反的改編策略,恰恰是出于同一種制作理念下的結果。那就是,盡可能滿足最大的潛在觀衆群體的需求。
對于騰訊版《三體》來說,它的主要受衆就是以國內科幻迷和三體迷爲主要群體的國內觀衆。這一群體最重要的訴求,就是看到原汁原味的《三體》原作被影視化。而之前藝畫版《三體》的慘狀,也證明了,在國內,“魔改”《三體》原作會是什麽下場。在這種情況下,騰訊版《三體》的制作,必然會采取盡量照搬原作的改編方式。

騰訊版《三體》海報。
而對于網飛版《三體》來說,面臨的就是另外一個情況了。網飛版《三體》的主創之一大衛·班紐夫在接受采訪時說道:“《三體》在中國很受歡迎,但在西方觀衆層面還沒有達到同等狀態,不過,我見過的來自中國的每個人都讀過《三體》,或者他們會說‘我家裏的每個人都讀過《三體》’。喬治·馬丁的書《權力的遊戲》甚至在改編之前就已經登上了暢銷書排行榜,但即便如此,你也必須做你認爲適合這一系列作品的事情,而且通常這意味著偏離文本。”
而網飛版《三體》1.6億美元的投資成本,也使得這部劇集必須得吸引足夠多的觀衆觀看,才能收回成本進而盈利。網飛版《三體》所做的這些改動,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爲了觀衆最大化。
據說,霍金的《時間簡史》出版時,出版商對他說:“一本書中多一個數學公式就會減少一半讀者。”同樣的,《三體》原作中那些最爲讀者稱道的,代表著科幻想象力極限的內容,在網飛的制作團隊看來,也是會導致觀衆減少的“公式”罷了。
這其中被诟病最多的改動之一,就是汪淼的“整個宇宙將爲你閃爍”。在原作中,“宇宙閃爍”是在微波背景輻射層面的整體震蕩。爲了看到這番景象,汪淼專門去到了中科院國家天文觀測中心的射電天文觀測基地。所有的這些鋪墊,是爲了說明宇宙背景輻射的長期穩定性。而三體文明能夠隨心所欲改動如此基本的物理現象,說明它們有著遠超人類的科技水平。
這也就是爲什麽,汪淼在看到宇宙閃爍時會有那種發自內心的震撼:“就這樣,他看到了宇宙背景輻射,這紅光來自于一百多億年前,是大爆炸的延續,是創世紀的余溫……他看到了天空的紅光背景在微微閃動,整個太空成一個整體在同步閃爍,仿佛整個宇宙只是一盞風中的孤燈。站在這閃爍的蒼穹下,汪淼突然感到宇宙是這麽小,小得僅將他一人禁锢于其中。”
所有的這些,對于閱讀《三體》小說的讀者來說,遇到硬核的內容,不管是放慢節奏,還是暫時跳過,又或者合上書本去查閱資料,然後再回來接著閱讀,都是合理的做法。但是,對于流媒體平台的電視劇來說,不管觀衆按下“暫停”按鈕,是停下思考還是去網上查資料,都是制作方想要盡量避免的。
正是在這種理念之下,網飛版的“宇宙閃爍”被魔改成了肉眼可見的“天空眨眼”。這當然顯得通俗易懂了許多。但是不可避免地失掉了原作中的魅力與內核。
基于同樣的理念,《三體》原作中的人物也被或者魔改,或者做了扁平化,簡單化處理。作爲主角團的“牛津五傑”,將原作中包括汪淼在內的科學家,變成了青春校園劇式的“夥伴冒險”模式。這既降低了原作硬核的門檻,也增強了作爲網飛主要用戶群體,美國青少年的觀看代入感。而包括葉文潔、史強等在內的角色也統一做了臉譜化的簡單處理,方便觀衆在第一時間理解他們的立場和態度。

網飛版《三體》劇照。
在此基礎之上,原作關于全體人類的宏大命題,被降格成了主角團之間互相産生愛恨情仇,一起去解決問題和危機的懸疑劇集,似乎也成了一種必然。
這不是網飛版《三體》這一部作品的問題,也不是網飛這一家的問題。甚至,全球的流媒體平台都存在這個問題。
有論文(《加速的碎片:新媒體環境下視頻播放行爲的時間轉向分析》)指出:“正如新媒體環境下,無論是視頻還是其他形式的媒介文化産品,生産者都竭盡可能地迎合受衆的需求,受衆因此也在一定範圍內獲得自主性。但是一味地迎合受衆的偏好,導致快餐式的文化消費愈演愈烈,同時在社會加速下,人們期待文化産品的呈現在時間上不斷壓縮,生産者因此依然保持著上位者的姿態來調配和控制文化産品,而原本需要投入時間和感情的文化産品也逐漸失去了靈韻。”
實際上,近幾年美國幾大流媒體平台制作的改編自經典作品的電視劇集,比如Apple TV+(蘋果公司的流媒體視頻服務)花重金基于阿西莫夫同名原作改編的《基地》,以及亞馬遜基于托爾金的原作改編的《指環王:力量之戒》,都有著與網飛版《三體》類似的問題。《基地》劇集完全沒有顯示出原作的宏大感,反而因爲劇情過山車式的快速推進被批評像“家庭倫理劇”。英國《衛報》的評論表示:“一整個銀河系的錢也救不了蘋果的星際垃圾。”

網劇《基地》第一季劇照。
例如,爲了讓盡可能多的觀衆可以無門檻觀看,所有涉及科學的硬核部分,都做了簡單化的處理。于是,在網飛版《三體》中,葉文潔要不厭其煩地解釋:“43+8=51”,說完之後還要對著一臉無法理解的楊衛甯說:“我已經簡化了。”而在《基地》劇集中,作爲整個銀河帝國中數學天才的蓋爾,劇集中表現她作爲數學天才的方式,就是讓她在一個人的時候默念素數。
同樣的,對于原作中複雜的劇情和設定,在劇集中都被扁平化,簡單化地壓成了一張大餅。例如,在《基地》劇集第一季的最後,面對兩個星球數百年間相互仇恨的戰爭。劇集給出的解決方法是讓謝頓本人機械降神式的出現,然後幾句嘴炮就消弭了仇恨與戰爭。而在《指環王:力量之戒》中,原作那複雜而又詳盡種族與勢力的設定,在劇集中也幾乎看不到多少體現。
這種制作理念,體現出的是當下時代以大數據爲導向,以最快速抓住用戶的快消品爲賣點的互聯網經營模式。而作爲天生就是互聯網公司的各大流媒體平台,會以這種理念來制作文化産品,也是一種必然。但是,對于那些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來沉浸其中,用心體會的經典作品來說,如此制作,難免會讓人覺得有些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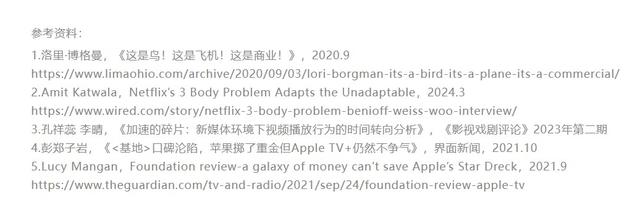
本文內容系獨家原創。作者:海客;編輯:荷花;校對:柳寶慶。封面題圖素材爲網飛版《三體》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

愛因斯坦有奶便是娘[得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