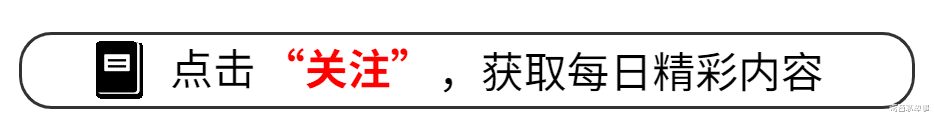
“你不要有什麽顧慮,我相信你一定能幹好!”錢三強看出了自己對面同志的顧慮,微笑著對他說。
1961年,爲了實現在科學上的領先,錢三強與劉傑商討後,決定成立輕核武器研究組,在確定了帶頭人是黃祖洽後,剩下的成員,有一個人很關鍵。
他是錢三強心中的最佳人選,但卻因爲政治問題,被許多領導直接否決。

可錢三強覺得,沒有他,研究組會失去很大一部分力量,且會將整個研究進程放緩。
這個人就是于敏,一個在曆史上幾乎被遺忘的科學家。
在那個政治動蕩的年代,重用于敏,無疑是一件具有極大風險的事。
即便如此,錢三強依然堅持自己的想法,力排衆議,最終讓于敏加入了研究組。

放眼我國大多有過極大貢獻的科學家中,幾乎都是留學歸來,而于敏卻說極少數中,沒有留過學的存在。
他是中國自己培養出來的科學家,畢業于北京大學,讀完碩士後,就進入了近代物理所工作。
很少稱贊別人的彭桓武都贊揚他,說他是“開創性的,是出類拔萃的人,是國際一流的科學家”。
日本著名核物理學家朝永振一郎率日本代表團來中國訪問,與于敏多有接觸,回國後發表的文章中稱他爲“國産土專家一號”。

丹麥物理學大師、諾貝爾獎獲得者玻爾和他接觸後,也稱贊他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大才,卻屢屢遭受政治運動的沖擊,公開批判他的“罪狀”如洪流一般湧來。
所以當錢三強找他商談,讓他加入到國家絕密工作研究中時,他整個人就像做夢一般。
用于敏的話來說,就是“感到非常突然,頭腦有點兒發蒙。”

在聽到錢三強的鼓勵後,他感到心頭一熱,眼裏含淚,重重地點了點頭。
于敏究竟做了什麽?才讓他被雪藏28年,一生也只是在受獎時,公開露面2次,連他的妻兒,都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
01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父親是一家企業的小職員,母親則在家裏忙活家務,帶孩子。
小時候,于敏就顯出了他驚人的才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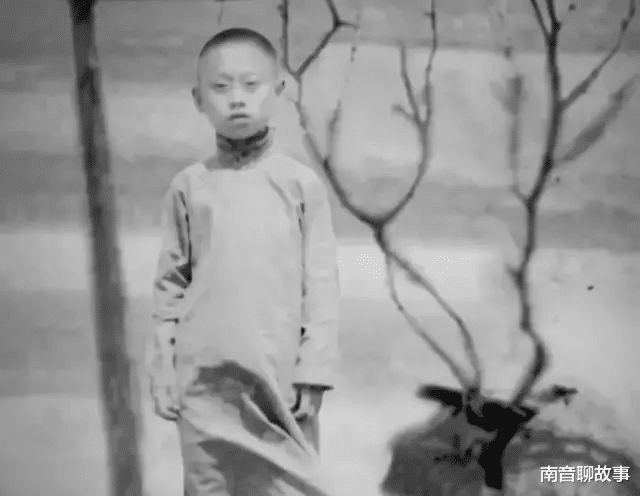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于敏卻酷愛讀書,整天在家裏,捧著一本書汲取營養。
父母看到孩子這麽用功,自然深感欣慰,也經常會跟他一起討論書裏的內容,偶爾父親也會說起國家大事。
聽得多了,愛國意識也在于敏的心裏種下了根,他立志要像嶽飛精忠報國那樣,發奮讀書,將來成爲國之棟梁。

所以但凡是書籍,無論是課內的還是課外的,是本書,于敏就拿來看,一看就是一整天。
他的成績在班裏,也是極好的,幾乎門門課都是第一,妥妥的學霸,天才中的天才。
高二那年,于敏的天賦開始被老師發現,他的恩師劉行宜決定培養他。
爲此他專門跑去于敏家裏,與他的父母深夜長談,只是爲了讓他能在更適合他的地方,發揮自己的天賦之才。

在老師看來,于敏的課外知識以及才學,在本校,已經無法滿足他的發展了。
在劉行宜恩師的強烈建議下,于敏被轉到天津最好的學校——耀華中學。
以于敏的家庭情況,本身是進不了這所學校的,如果不是劉行宜老師公開擔保,于敏恐怕會與之錯失交臂。
在人生路上,能遇到這樣一位恩師,不可謂不幸運啊!

于敏入校以後,也果然不負衆望,永霸學校第一的寶座,尤其在物理科目上,極爲突出。
1944年,于敏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理學院,因爲他的成績名列榜首,還沒開學就引起了老師的注意。
他的導師張宗遂曾說:“沒見過物理像于敏這麽好的”。
這或許注定了于敏的一生,將與物理結下深深的緣分。

大學期間,他的父親因病重,家裏失去了唯一的經濟來源,于敏也差點被迫退學。
在同學陳克潛的幫助下,于敏才得以返校繼續學業。
陳克潛當時認爲,如果像于敏這樣的人才,只是因爲經濟貧困而中止學業,那對于中國的未來將是一大損失。
北大這個大學堂裏人才濟濟,全國各地的尖子生,幾乎都在北大和隔壁的清華,可于敏進來後,也絲毫不遜色于人。

縱使周圍高手雲集,于敏在學習上便更加刻苦,所以名列前茅對他來說,絕非難事。
同學們都說他是超級學霸,因爲一次較難的數學考試,作爲旁聽生的于敏,卻拿下了滿分100分的好成績。
而當時北大最高的分數不過60分,都說一分能壓倒一片人,他遠遠超了40分。
那一次,他成了北大許多學生的偶像。

這真的就不是刻苦努力的事兒了,是于敏的智商本就高于普通人。
在考學的路上,于敏永遠是第一。
本科畢業後,他繼續攻讀碩士,並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在了物理系張宗燧的名下,與恩師一起主攻量子學。
碩士期間,于敏的表現依舊驚人,他憑借著超高的理解力和記憶力,使得一貫嚴苛的張宗燧,都忍不住誇贊他。
然而工作以後,于敏甘願收起身上的光芒。

02
1951年,于敏被推薦到物理研究所工作,依然從前量子場的理論研究,這與他的興趣剛好一致。
然而這個時期,正是我國抗美援朝爆發時期,美國曾多次揚言,要用核武器踏平我們的國土。
那個時候,我國科技在核武器領域,可以說是一片空白,如果敵人真使用核武器,我方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我國許多研究科技領域的學者專家開始覺醒,他們意識到,想要不被欺負,就必須要有與他國相抗衡的有力武器。

當時,也是錢三強找到于敏,讓他從量子場的研究,轉向原子彈研究。
于敏二話沒說,直接放下手裏的項目,轉到還是一片空白的原子彈領域。
可想而知,研究開展起來有多難,從0到1的跨越,恐怕也只有于敏了。
他花了僅僅四年的時間,就在這一領域有了重大突破,並且出版了我國第一本原子彈領域的書籍,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

因爲在研制核武器的權威物理學家中,因于敏沒有任何留學經曆,因此他被親切地稱爲:“國産土專家一號”。
然而正當他在原子基礎科學研究方向,培養了極大的興趣時,錢三強的一句話,他又立馬調轉了方向。
1961年1月12日,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
錢三強找到于敏,進行了一次嚴肅和秘密的談話,希望他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從此改變和決定了于敏此後的人生道路。
于敏當時只說了一句話:“愛國主義壓過興趣,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
錢三強拍了一下于敏肩膀,鄭重地說:“咱們一定要趕在法國之前,把氫彈研制出來!”

就是這一次選擇,于敏從此隱姓埋名28年,卻無一聲怨言。
許多人不知道的是,原子核理論研究與氫彈研制有很大差別:一個是純理論,埋頭苦幹就行;一個是應用科學,以實踐爲主;前者是公開的研究,後者是絕對保密的。
對此,于敏有過短暫的猶豫,畢竟要放棄自己熟悉的領域,還要隱姓埋名幾十年,換了誰,都得思量一番。

在當時那個惡劣的環境中,因爲火熱的政治運動,于敏顯然是不被信任的。
當錢三強破除萬難找到他,並給了他如此重要的工作,他心裏感激,也明白此項工作在國家發展中的重量。
于敏在多年後的自述中也曾寫道:“現在我們國家要強國富民,要搞原子彈、氫彈,防禦外來侵略,這是一個曆史性的任務,也是我實現夙願,報效祖國的機會。”
這項技術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屬于高級機密,所以于敏面對的,又是一項空白,一群人在河裏摸著石頭過河。

03
然而在研究的過程中,他們要面對的不僅僅是技術上的困難,還要克服許多外部客觀條件,比如:在大山戈壁裏寒冬的難耐,長眠面對各種理論和機器的寂寞,還有來自國家最高期待……
那個時候,國家一窮二白,連建造實驗廠區的財力都沒有,而核爆級的計算量,大到驚人,他們只有一台每秒5萬次運算量的計算機,如果只靠它,估計得幾輩子。
于敏和黃祖洽、何祚庥一起,領導原子能研究所“輕核理論組”,帶領30名科研人員,在4年中做了大量預先探索研究工作。
他們30幾個人,經常因爲一個理論,一個實驗,爭得面紅耳赤,大家各有觀點,但最終又能彙聚成一點,這絕對是最強團隊必須具備的素質。

憑借著衆人齊心,加上于敏驚人的記憶力算法,終于在4年後,于敏等人實現了氫彈原理的突破,他興奮地給鄧稼先打去電話:
于:“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只松鼠。”
鄧:“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于:“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但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
鄧:“好,我立即趕到你那裏去。”
作爲好友,更是科技前沿的脊梁,鄧稼先二話沒說,就去到了大山裏。

爲了搶在文革帶來的嚴重沖擊之前,幾個小組經過了一百多個日夜的推理演算,反複試驗,終于來到了具有曆史紀念意義的時刻。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圓滿成功,僅僅只用了2年零8個月。
1967年6月17日,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爆炸威力同于敏計算的結果完全一致。
那一夜,于敏因爲不在現場,只是聽到成功這兩個字,他就已經淚流滿面。

他說,那一晚,是他多年來睡得最踏實的一個晚上。
我國成功趕在了法國的前面,當時的戴高樂總統怒拍桌子;美國也不敢小觑中國,美國軍方直言:這家夥可抵十個集團軍;日本聽了直接發懵。
于敏,就是那個在中國氫彈原理突破中起了關鍵作用的人。

1984年,在新疆核試驗基地的討論會上,因陳寬心血來潮吟誦的《出師表》,引起了于敏的共鳴,他的偶像除了嶽飛,還有機智的諸葛亮。
這時,只聽到:“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這場會議上,于敏一個人從頭到尾一字不落地吟誦完畢,當念完最後一句話時,在場的所有人都泣不成聲。
直到1988年于敏被解密,美軍才不得不相信中國竟然有這樣的人才,卻在一邊酸溜溜地說:于敏是上帝派給中國的作弊器。

然而因爲多年的研究,給于敏的身體造成了強大的負荷,研究時他幾乎沒有認真吃過一頓飯,這也讓他患上了嚴重的胃病,身體虛弱到幾次休克,差一點被死神帶走。
但革命尚且要繼續,他不能倒下,這關乎國家的命運,更決定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在鄧稼先去世後,于敏仍然奮戰在一線。
2015年,面對榮譽和鏡頭,于敏說:“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當聽到人民說他是“中國氫彈之父”的時候,他卻表示不敢當,這功勞是大家的,一個人是做不出來的。
盡管話雖如此,但于敏在這場長時間的戰爭中,所發揮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沒有他,我們不可能成爲五個核大國之一;因爲他,世上僅有30枚可用氫彈均在中國。
于敏這一生,對國家無愧于心,晚年時深感對妻子和家人的虧欠,至于榮譽和金錢,他都看得很淡薄,從他家客廳內挂著的裱字就能看出:“淡泊以明志,甯靜以致遠”。

2019年1月16日,93歲的于敏,悄然地離開了我們,但這顆巨星,將永遠挂在星空之上,耀眼璀璨。
在世時只有兩次公開露面,一次是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1999年),一次是榮獲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2015年1月9日)。
如果不是因爲熱愛生養他的祖國,也許于敏也早就像某些科學家那樣,離開中國,去尋找更寬廣的天地去了。

我慶幸,生在華夏之土,周圍有一群像于敏、錢學森、郭永懷、王承書、鄧稼先……這樣的科學家,是他們爲我們掙得了一方淨土,造福了千秋萬代的子孫。
致敬于敏,致敬所有在核武器領域做出貢獻的科學家。
希望有朝一日,他們的名字都能夠出現在課本之上,成爲鼓舞我們後世的不滅源泉。
圖片來自網絡
侵權請聯系作者刪除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