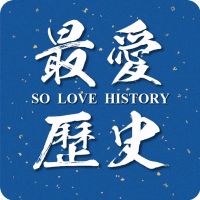在那次改變北京大學,乃至新文化運動的曆史性會面之前,蔡元培與陳獨秀已經是老相識了。
他們一起造過炸彈。
清末,爲刺殺滿清大員,蔡元培與朋友們組織了暗殺團。蔡元培後來談起這段履曆時說:“36歲以後,我已決意參加革命工作,覺得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
蔡元培在上海租了個房子,親手制造炸彈,他找來章士钊幫忙,章士钊又找來了陳獨秀。
據陳獨秀回憶,他從安徽一到上海就加入了這個組織,住在上海月余,天天跟著試驗炸藥。
這一切似乎不可思議,但在救國圖存的探索中,這些讀孔孟之道長大的書生都甘于抛頭顱、灑熱血,爲革命獻身,诠釋愛國青年之血性。
十多年後,1917年,在一個黎明之前的覺醒年代,這兩位大師再次相遇。

▲北京大學第二屆文科哲學門畢業生與老師合影:前排右4蔡元培。
愛國心與自覺心正如魯迅先生在《小雜感》中所寫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這便是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時局。
幾經風雨,幾經磨難,到了1915年,包括陳獨秀在內的革命黨人,已經曆清帝遜位、二次革命等走馬燈似的政治大戲,推翻了滿清,建立了民國,卻依舊看不到國家的未來,心好累。
與此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列強在華利益重新洗牌。日本以協約國之名參戰,實則趁火打劫,派兵占據了膠州灣租借地和膠濟鐵路全線,搶占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並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野心勃勃地想要獨占中國。
這一年,陳獨秀正處于人生低谷。此前,他因參與二次革命失敗,一度被袁世凱的親信列爲通緝犯,不得不告別妻兒,流亡日本。
在日本期間,陳獨秀與胡漢民、章士钊等辦起了《甲寅》雜志,抨擊時政。這本刊物的主要撰稿人,還有時年26歲的李大钊,以及高一涵、易白沙等愛國青年。

▲陳獨秀(1879-1942)
陳獨秀與李大钊最初相識,卻引發了一場關于愛國問題的爭論,可謂“不打不相識”。
在該刊中,陳獨秀第一次以“獨秀”的名字發表了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批評國人漠視國事,不理解國家爲何物。
陳獨秀不吐不快,如一個憤青,發泄對現實社會的不滿,說西方人所講的愛國,與中國人的忠君愛國“名同而實不同”。歐美人視國家爲“國人共謀安甯幸福之團體”,而當時的中國人,卻仍將國家當做封建王朝的家天下,“凡百施政,皆以謀一姓之興亡,非計及國民之優樂。”
辛亥革命革了個寂寞,執政者以舊的方式執政,民衆也遵守舊的思想觀念,仍然以草民自居。這才有了袁世凱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複辟鬧劇,以及一些人高喊奉孔教爲“國教”的落後思想。
這篇文章中,陳獨秀流露出革命失敗後的彷徨苦悶,也在苦苦追尋新道路。但是,文中痛陳國家極端黑暗,毫無可愛之處,甚至故作危言,說與其如此,不如當亡國之民爲好,不少中國留日學生對這種言論感到不太舒服。
于是,李大钊作爲代表,在1915年8月的《甲寅》第1卷第8號上發表《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對陳獨秀的消極態度進行了溫和的批判,說其“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義嫌其太少”。
李大钊這篇文章的意思是,既然您覺得國家不可愛,那我們更要改變舊秩序,改造國民性,喚醒國人的自覺心呀。
興許是受到李大钊等人的啓發,陳獨秀産生了新的覺悟。一個月後,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了《青年雜志》。
敬告青年1915年6月,陳獨秀妻子高君曼生病咳血,陳獨秀接到好友汪孟鄒的來信後迅速回國,與妻兒居住于上海法租界。
高君曼是陳獨秀續弦之妻,也是他元配夫人高曉岚的妹妹。這段有違世俗的婚姻難免讓人說閑話,陳獨秀的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也因此跟他們爸爸鬧別扭,多年來缺乏聯系,常年在外漂泊。
這倆年輕人跟他們父親陳獨秀一樣倔強,甯肯出去當打工人,睡在上海亞東圖書館的地板上,也不肯接受家裏的經濟援助。
作爲繼母兼姨母的高君曼于心不忍,托人說情,讓陳獨秀把孩子接過來一起住。陳獨秀卻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聽他們自創前途可也。”
當時,陳延年兄弟信仰的是巴枯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他們攢夠錢,到上海求學,考取了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震旦大學,並在之後赴法勤工儉學。
據見過陳延年、陳喬年的人回憶說,這兩兄弟的模樣就像清教徒,“吃得壞,穿得壞,絕口不談女人”。多年後回國,他們改變了思想,終于成爲父親陳獨秀的同志,卻走向悲壯的結局。
1915年回國後,面對民族危亡的困局,陳獨秀漸漸從意志消沉中走出。
陳獨秀認爲,當務之急是發起一場反封建的思想運動,仿造歐洲的文藝複興、啓蒙運動,爲全民帶來新思想、新文化,讓他辦個八年十年雜志,一定能使全國思想改觀。陳獨秀沒錢,只好將這一想法告訴私交甚密的安徽老鄉汪孟鄒。
汪孟鄒當時是亞東圖書館的經理,欣然同意好友的創業想法,並由他出面介紹,拉來了群益書社的老板陳子沛、陳子壽兄弟給陳獨秀投資,議定雜志每月的編輯費和稿費爲200元。
經過多方奔走籌備,1915年夏天,這本叫《青年雜志》的刊物橫空出世,最初的發行量只有1000冊。一般認爲,這是新文化運動發端的標志。
因爲《青年雜志》跟當時的《上海青年》周報名字有些雷同,所以到了第二卷時,《青年雜志》正式改名爲《新青年》。

▲《青年雜志》創刊號封面
在發刊詞《敬告青年》中,陳獨秀樹立起了民主與科學的旗幟,熱情地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人生最可寶責之時期也。青年之于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
陳獨秀將希望寄托于那個年代的“後浪”身上,希望青年自覺擔起救國救民的重任,進而對青年提出了提出六個標准:
自由的而非奴隸的;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從此以後,陳獨秀聯合志同道合的戰友,爲了喚醒民衆,對幾千年來中國封建文化中最落後、保守、反動的愚昧迷信、舊道德與舊文學發起了猛烈的攻擊。
這本叫《新青年》的雜志,將改變一個時代。
李大钊經過與陳獨秀的愛國辯論後,也成了陳的好友。聽到陳獨秀的呐喊聲後,李大钊也在次年回國,成爲其有力支持者,于《新青年》發表了《青年》一文,洋洋灑灑8000多字,用115個“青春”呼喚青年覺醒,讀來令人激情澎湃。其中寫道:
進前而勿顧後,背黑暗而向光明,爲世界進文明,爲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在新舊思想的對壘中,《新青年》面對著來自保守者的巨大壓力。作爲主編的陳獨秀,甯可斷頭流血,也毫不退縮,他說:“西洋人因爲擁護德(Democracy,民主)、塞(Science,科學)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塞兩先生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一切的黑暗。”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封面
1917年,注定是《新青年》的裏程碑之年。正是在這一年,新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邀請陳獨秀與《新青年》北上。
據當時北大部分教師的回憶錄記載,1916 年,陳獨秀爲辦《新青年》跑到北京募款,正好北大要引進人才,缺一名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
經過友人引薦,蔡元培翻閱了《新青年》後,決定聘請陳獨秀到北大任教。陳獨秀起初不答應,他對其他朋友說:“蔡先生約我到北大,幫助他整頓學校,我對蔡先生說,我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什麽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更何況,陳獨秀還要主編《新青年》,事務繁忙。
蔡元培親自登門拜訪,告訴陳獨秀,沒有頭銜不礙事,我們不搞論資排輩,還請他把《新青年》也搬到北京來辦。陳獨秀只好答應試幹三個月,如果勝任就繼續幹下去,如不勝任就回上海。
雖然一起做過炸彈,但蔡元培的辦學能力更能讓陳獨秀放心。
蔡元培在北大任職期間,倡導思想自由,主張兼容並包。他認爲,在現代國家,思想與言論的自由是第一原則,在大學更是如此,若大學裏沒有思想自由,就算不上大學,這就是所謂的,“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爲大也。”(《<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

▲蔡元培(1868-1940)
陳獨秀答應了老戰友的邀請,這也意味著,這場空前的思想運動從此將與中國的最高學府緊密相連,蔡元培實際上成爲了《新青年》編輯部的保護者。
這一年,在張勳複辟時南避上海的李大钊,也應北京大學之聘請北上,擔任北大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圖書館主任。
同年8月,一位青年學者在日記本中寫下《伊利亞特》第18章第125行的譯文,“如今我們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之後從美國起程歸國,掀起一場白話文運動。
他是胡適。
到了北大後,這名27歲的安徽人成爲全校最年輕、薪水最高(月薪280元)的教授之一。他與51歲的蔡元培、39歲的陳獨秀都是卯年生人,組成了“三只兔子鬧北大”的文化盛況。

▲北京《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文學改良刍議胡適認爲,有三本雜志,可以代表三個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正如胡適所言,《時務報》代表戊戌變法時期,《新民叢報》代表清末維新派與革命派對政體問題進行激烈辯論的時代,而《新青年》,代表著新文化運動。
這只“兔子”,有一顆文學革命的心。在康奈爾大學留學期間,他就給朋友寫信說:“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觀!”
在胡適的回憶中,他發起文學革命的起因,出于留學期間的一段經曆。
作爲一名庚子賠款生,少年胡適每月都要從華盛頓的中國公使館領取一筆生活津貼,而當時清華留美學生監督處的一個書記先生受了傳教士的影響,經常利用機會印一些傳單給老外做宣傳,大致內容是“不滿二十五歲不得娶妻”、“廢除漢字,取用字母”等。
有一天,胡適又一次看到了這些宣傳語,說什麽“欲求教育普及,非用字母不可”。胡適一時動了氣,寫一封信去罵對方,說:“你們這種不通漢文的人,不配談改良中國文字的問題!”
可見,胡適反對盲目的全盤西化。他認爲,文言文是半死之文字,要讓中國文字“活”過來,就要普及白話文。

▲青年胡適
1916年,經過安徽同鄉汪孟鄒牽線,胡適與陳獨秀開始書信往來,並成爲《新青年》的編輯。胡適說,陳獨秀是個老革命黨人,也是文學革命的急先鋒,有他這樣一位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推行者,不久就要形成一個“大力的運動”。
在陳獨秀的支持下,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表文章《文學改良刍議》,認爲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呻吟,五務去濫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
有趣的是,這篇提倡白話文運動的文章卻是用文言文寫的。
在收到胡適的《文學改良刍議》後,作爲主編的陳獨秀也揮動如椽巨筆,立即寫下了《文學革命論》,與《新青年》同人一同推動“白話文爲文學正宗”。正是有了這一代學者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普羅大衆都能運用自如的白話文。
這一時期,胡適與思想保守的衛道士之間發生了不少趣事。
在後來的特殊年代都堅持寫文言文的章士钊,也曾于擔任段祺瑞政府的教育總長期間反對白話文,提倡舊道德。
有一次,胡適與章士钊一起照相。章士钊特意在照片上題了一段白話文送給胡適,說:
“你姓胡,我姓章。你講什麽新文字,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做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適見狀,也特意回了一首舊體詩,對章士钊表示尊重,以和爲貴:“但開風氣不爲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

▲胡適與章士钊合影及題跋
當時,北大還有不少章太炎的門生,如黃侃,也反對白話文運動。
黃侃故意調侃胡適,說:“胡適之先生口口聲聲要推廣白話文,我看您未必出于真心。”
胡適一聽納悶了,說,黃先生此話怎講?
黃侃笑道:“如果胡先生身體力行的話,大名就不應叫‘胡適’,而應改爲‘往哪裏去’才對呀!”這些大師如果去吐槽大會,也沒其他嘉賓什麽事了。
胡適對這些刁難一一進行反擊。有一個老北大廣爲流傳的故事,說是有一次上課,一個同學激憤地反對白話文:“白話文不夠精練,打電報用字多,花錢也多。”
胡適舉了個例子,說前幾天有位朋友給我打電報,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願從政,決定不去。爲這件事我要複電拒絕,不妨請同學們用文言文來寫一複電,看看究竟是白話文省字數,還是文言文更簡潔?
學生們都躍躍欲試,最後選出字數最短的一個答案,共12字:“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胡適笑了,說我的白話電報,只用了五個字——“幹不了,謝謝。”

▲胡適在寫作
胡適並非孤軍奮戰。
當時,《新青年》的另外一名著名編輯劉半農在致同事錢玄同的信中說:“你、我、獨秀、適之,四人,當自認爲‘台柱’。”
陳獨秀、胡適、錢玄同與劉半農,是《新青年》的四大台柱。
1917年,只有高中肄業學曆的劉半農也接到蔡元培的邀請,成爲北大預科國文教授。正是蔡元培不拘一格選人才,才有北大兼容並包的氛圍。
劉半農在《新青年》出版第2卷時加入編輯部,與陳獨秀相見恨晚,他翻譯了大量世界名著,寫了不少反映窮苦人民的新詩,批判了當時存在的許多不公平現象,如他的第一首白話詩《相隔一層紙》,寫一個屋子裏點著爐火,屋內的老爺吩咐人說:“天氣不冷火太熱,別任它烤壞了我。”隔著一層薄紙,屋子外卻躺著個叫花子,咬緊了牙齒,對著北風喊:“要死!”
對我們今天的人來說,劉半農還有一個巨大貢獻,就是創造了用來稱呼女性的“她”字。
漢語中原本沒有與英語的“she”相對應的字,劉半農在他所寫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中率先使用了“她”字,影響至今。

▲1920年,劉半農與妻女
在編輯《新青年》第4卷第3號時,劉半農與錢玄同唱了一次雙簧戲,宣傳文學革命。錢玄同化名王敬軒,以保守派的身份寫文章對劉半農進行種種責難。劉半農自導自演,對“王敬軒”的責難一一批駁,嬉笑怒罵,躍然紙上。
這場辯論,被稱爲“現代中國報刊史上精彩的一筆”。現在媒體人玩的這一套,都是老前輩們玩剩下的,依舊屢試不爽。
自稱爲《新青年》搖旗呐喊一小卒的錢玄同,是新學與舊學的“混血兒”,他與黃侃等人同爲古文學家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又留學日本,接受過新式教育,堅決地反帝制、反複古。錢玄同還有個了不起的兒子,即中國“兩彈一星”元勳錢三強。
作爲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員猛將,錢玄同比胡適激進得多。他有不少驚世之語,其中一句是說:“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槍斃。”
因此,在1927年錢玄同40歲生日之前,他的幾個朋友特地在報刊上發了一期《錢玄同先生成仁專號》,上面全是訃告、挽聯之類的稿子,老搭檔劉半農更是寫了一篇《祭玄同文》。實際上,錢玄同當時身體還好著呢。
值得一提的是,錢玄同在當《新青年》編輯時,還催生了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魯迅。

▲晚年錢玄同夫婦與兒子錢三強
狂人日記1912年,公務員周樹人隨教育部遷北京,居住于紹興會館,最初幾年的生活苦悶而消沉,書倒是買了幾百冊。周樹人無聊時就枯坐書房,只做兩件事,一件事是謄抄古碑,另一件也是謄抄古碑。
周樹人在北京的數年間,中國社會處于劇烈的動蕩之中。
1913年,孫中山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
1915年,袁世凱複辟帝制,蔡锷等發動護國戰爭。
1917年,張勳複辟鬧劇收場,各路軍閥依然混戰不休。
山河破碎之際,憂國憂民的周樹人躲進自己的小屋,深埋故紙堆中。對于周樹人消極遁世的生活態度,好友錢玄同很不贊成。

▲周樹人、周作人兄弟與愛羅先珂等朋友合影
有一夜,錢玄同前去周樹人家中,翻著那些古碑、古籍的抄本,說:“你抄這些有什麽用?”
周樹人坦然回答:“沒有什麽用。”
“那麽,你抄它是什麽意思呢?”
“沒有什麽意思。”
錢玄同突然認真地說:“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周樹人懂錢玄同的意思,他們正在辦《新青年》,也許是感到寂寞了,想要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
可周樹人還是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被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而且從昏睡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爲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爲對得起他們麽?”
錢玄同答道:“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這次嚴肅的長談,後來被周樹人寫入短篇小說集《呐喊》的自序中。
周樹人再次翻開書,悲涼地審視那個殘破的時代,他拿起筆,開始寫:“我翻開曆史一查,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他仰天長歎:“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他振臂高呼:“救救孩子!”
1918年5月15日,在《新青年》第4卷第5號上,周樹人發表了中國第一篇現代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猛烈抨擊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如同一聲驚雷,響徹中國。
這也是周樹人第一次使用“魯迅”這個筆名。陳獨秀讀完這篇小說,由衷地發出贊歎:“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
自《狂人日記》起,魯迅一共在《新青年》發表作品50余篇,他與同人們向青年傳遞了民主、科學、獨立的思想與新文化觀念,也將底層民衆的心聲告知世人。
魯迅說,《新青年》的催稿就是他創作的動力,“《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先生說過,時間就像海綿裏的水,但他說了,自己也是個拖延症患者。

▲魯迅(1881-1936)
庶民的勝利到北大任職後,李大钊結束顛沛流離的日子,生活總算得到改善。
當時,北大教職員的待遇十分優厚,李大钊月薪爲140元(後來漲到200元),這個數字在當時可以供養三十口人。李大钊卻將這筆錢用于學術研究與革命運動,以及資助北大的貧困學生,自己依舊過著粗茶淡飯的生活。
那幾年,每到開學季,北大很多貧困學生就會收到一個名曰“無名氏”寄來的彙款,直到多年以後,大家才知道這個“無名氏”是李大钊。
哲學系的學生劉仁靜就得到過李大钊的資助。李大钊對北大的相關部門說:“劉仁靜君學宿等費由鄙人暫爲擔保,一俟家款寄到,即行繳納不誤。”
現在,還有一張李大钊親筆寫的字條留存:“劉仁靜同學學費先由我墊。李大钊。”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俄國革命起初並沒有引起李大钊的注意。
在他眼中,俄國人直到二月革命時也不過是在走中國人的老路,而非後來說的,中國人走俄國人的路:“平心論之,俄國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國曆次革命之影響。”
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爲李大钊送來了新的思想,並將徹底改變此後百年的曆史。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先後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
覺醒年代,翻開了新的篇章。

▲李大钊(1889-1927)
《新青年》的“新青年”們,沒有一個人空喊口號,他們都在爲救亡圖存而艱苦探索。
李大钊到農村去,到車間去,親身了解煤礦工人的生活狀況。他告訴青年:“只要你的光明永不滅絕,世間的黑暗,終有滅絕的一天。”
陳獨秀作爲《新青年》的主編,爲德先生、賽先生與新文學搖旗呐喊,之後,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胡適提倡白話文,奠定了中國現代學術與語言的基礎。
魯迅是新文學的導師,他筆下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閏土等人物,就是現實世界的縮影。
從1915年9月15日創刊到1922年休刊,《新青年》走過了7個年頭,之後在1926年7月終刊,共出版63冊。
《新青年》吹響了青年爲救亡圖存而解放思想的號角,培育了整整一代年輕人。
湖南省立第一師範一位姓毛的學生,以筆名“二十八畫生”,在《新青年》第3卷第2號發表了文章《體育之研究》,全文提倡“體育興國”,充滿朝氣蓬勃的青年人生觀:“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苟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
後來說起陳獨秀時,他說:“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
從1919年開始,蔣介石也對《新青年》情有獨鍾,從目前公開的蔣介石日記中可以看到,直到1926年他率領北伐軍北伐,都沒有放下這本雜志。
無私無畏的李大钊,于1927年被張作霖送上絞刑台,臨終前神色未變,從容赴死。犧牲後,他家沒錢安葬,社會各界發起募捐,進行公葬。
據說,連政見相左的汪精衛也捐了1000 塊大洋。錢玄同爲解決李大钊子女生活的困窘,至死都拖著病體爲李大钊家人籌錢。

▲李大钊犧牲時的新聞報道
陳延年、陳喬年兄弟放下與父親陳獨秀的恩怨,回國參加革命。
1927年6月,陳延年秘密轉移時不幸被捕,于是隱藏身份,自稱是工人陳友生路過,轉托父親的友人汪孟鄒營救。汪孟鄒找到了胡適,胡適便請陳延年的老師吳稚晖幫忙。但因陳延年曾受教于吳稚晖講授的無政府主義,後來轉變了思想,而且陳獨秀還罵過吳稚晖爲老狗,吳對此耿耿于懷,不願出手相救,反而使陳延年的身份暴露。
7月4日,陳延年被處決于龍華刑場,因不願下跪,站著被劊子手亂刀砍死。直到此時,汪孟鄒和胡適才知道求錯了人,爲此抱憾終身。
次年,陳喬年也遇害,兄弟二人一年之內相繼被捕,英勇就義。

▲陳延年(左)與陳喬年(右)
那時候的青年,心懷理想,並爲此甯死不屈。
作爲“新青年”之一的魯迅,曾在《熱風·隨感錄》中如此寄語年輕人: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這就是,中華民族偉大的覺醒年代。
參考文獻:
胡適:《四十自述》,人民日報出版社,2013
羅志田:《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陳利明:《陳獨秀傳》,團結出版社,2011
陳光中:《走讀魯迅》,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
[美]基辛格:《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5
[美]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張耀傑:《北大教授與<新青年>》,新星出版社,2014
耿雲志:《<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的百年回響》,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年第06期
桑兵:《北京大學與新文化運動》,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7年第05期
張家康:《<新青年>的四大台柱》,傳記文學2017年第02期
郝思斯:《從<覺醒年代>看覺醒》,中國紀檢監察報,2021-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