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四十年,
現在的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有些東西是走不出去的。
這四十年,那個村子一直都在我身邊,
它在我的血液裏,在我的靈魂中,
我當年是帶著它上路的。
我十六歲離開家鄉,四十余年的出走並沒有真正遠離那個村莊。我的父母還在那裏,老屋還在那裏,我的那些記憶的證物還在那裏。
我不斷地重返故鄉,與親人和記憶重逢。
一
我的家鄉在遼西,我家的屋後就是那道著名的柳條邊,我們在邊裏,這是漢族和滿族的居住區,邊外是蒙古族和漢族的雜居地。蒙滿漢三個民族、三種文化在漫長的共處中相互融合卻也還各自保持著自己的特質。

韓春燕老家街巷一角。
我們村莊的名字竟然是個副詞:朝北。原來後邊還有兩個字:營子。全稱應該是朝北營子,後來爲了簡便就改成了朝北。據說這裏從前是驿道,原本是駐紮有兵營的。這個“邊”上的村子很大,有集市,單日開集。開集日,邊裏邊外的村民趕著車馬,推著自家的糧食果蔬,彙集于此,從西到東一條長街人頭攢動,煞是熱鬧。
有些姻親就是在集市上結下的,有些故事就是在集市裏開始的,集市成了蒙滿漢村民的社交平台,也成了把三個民族緊密連接起來的紐帶。
我小的時候,集市是我的樂園,江家館子在集市炸出的麻花,我祖父說被我吃了幾花簍,祖父這麽說是爲了證明我作爲他家的長孫女是多麽被寵。
我是一個被寵愛的孫女。祖父祖母只有父親一個孩子,祖母說還有個女孩三歲時夭折了,可能是失去了女兒的緣故吧,我從出生就得到了祖父祖母無比的珍視和寵溺。我的頭發從胎毛留起,很小就擁有了長長的麻花辮,我的衣服繡滿了花朵,哪怕半夜餓了想吃餃子,祖母都會起來抖一抖面袋子給我包一碗餃子。人說孩子是會被嬌慣壞的,好在祖父祖母的仁厚和善良給了我更多的正面影響,我沒有成爲那棵長歪的小樹,而自小得到了太多的關愛,也讓我能夠以善良之心對待周圍的人和這個世界。
我十六歲離家去城市讀書,那個時候的我兩條長長粗粗的及腰麻花辮,自己甚至都沒有親自洗過,沒了祖母的照顧,那時候也沒有什麽洗發劑,我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打開能裝滿一大盆的頭發,只好剪掉了辮子,留起了短發。
我在祖母的衣襟下長大,我無法想象離開祖母的生活,我憧憬將來我工作了要把祖父母接過來,我們一起生活。然而,他們並沒有給我孝敬的機會,祖父在我高中畢業那年的端午節前辭世,祖母在我大學畢業的第三年秋天離開。他們對我山高水長的恩情,我此生再無法報答。
那個村莊的向陽山坡埋葬著我的祖父祖母,這是我跟它永遠無法真正告別的理由。
二
當然,祖父祖母不在了,這個村莊還有我的父母,有我從小到大的朋友。我每一次回村都要趕一趕大集,都要跟早年的夥伴們見一見聊一聊,聊誰誰誰怎麽樣了,聊過去的點點滴滴,而且年齡越長懷舊的成分越多。
我家前面鐵匠鋪的老板娘是我小學同學,我倆一直保持親密的交往,是源自當年我倆一起多次逃學結成的友誼。在我女兒小學還沒畢業時,她就已經當上了奶奶,她開朗活潑幽默,是一個樂觀的女人。我每次回家,她都高聲大氣地嚷嚷,哎呀,你看你還沒啥變化,我都是個當奶奶的老太太了,語氣裏並無對我沒變化的羨慕,而是當奶奶的滿滿自豪。就是這樣開朗的一個人,最後死于被妯娌辱罵後的想不開,活活氣出病來,最後被氣死了。
村莊站在那裏,時間的印記,命運的輪轉,都是那麽清晰。一代代人出生,一茬茬人離開,在村莊,人如同莊稼,眼見著長大,眼見著衰老,眼見著先後被收割。
好在,集市還在,集市兩邊那些低矮的磚房已經換成了一幢幢二層樓房,街路也早就鋪上了水泥,趕集的人換了一茬又一茬,那些還在的卻也換了面孔——鄉野的風硬,鄉野之人就老得快。

故鄉的變不僅僅這些,幾年前回村,柳條邊的樹已被砍光了,柳條邊的土據說也被挖走賣掉了,柳條邊只剩下一個碑石孤零零地立在道邊。得知是村裏有權勢的人把柳條邊的土和樹飽了私囊,出于對村霸的無知與無所顧忌的氣憤,我把這個情況反映給了當時的縣委書記——他是我同學的愛人,他很重視,馬上就電話了我們所在鄉的領導,鄉裏領導又電話問詢了我們村的負責人,無疑這是一個死循環,結果可知。
不過,立在那裏幾百年的柳條邊沒了,少了界限,也許邊裏邊外的文化更少了差異了吧。
故鄉的面貌總的來說呈現一種奇怪的狀態。一方面是好多人家蓋成了闊氣的大院套的樓座子,那些瓷磚在陽光下白得刺眼,而正街更是有了成排的樓房和超市,那些平坦堅硬的水泥路在村莊縱橫交錯,使村莊的氣質更貼近城鎮,而另一方面村莊也有很多坍塌廢棄的老房子,那是離鄉的人家丟下的,他們大多是年紀大了去投奔了城裏的兒女。現在村子裏的年輕人結婚,男方大多要在縣城買個房子的,年輕人誰也不願意留在村裏。他們去城市打工,但一般在城裏是買不起房子的,于是縣城便成了他們最多的選擇。
三
村子是老年人的村子,在村道上溜溜達達的大多是上了年紀的人。
我的父母就在這個人群裏,他們堅守的決心我們誰也動搖不了。我的父母都是鄉村知識分子,父親做過完全中學的校長,吹得笛子拉得二胡還寫得一手好字。我們姐妹兄弟五個,大家都在城市居住,這些年一直動員父母到城市,他們不爲所動。母親後來腿腳不太方便,是父親一直照顧母親。父親把老宅的房前屋後收拾得幹幹淨淨,院子裏每到春夏開滿鮮花,兩棵甜李子樹年年都碩果累累。父親還在後園子種下各種蔬菜,每當我們回來,他除了給我們准備一桌好吃的飯菜,走時一定還要給我們帶這帶那。父親清楚我們每個人的喜好和口味,如同母親記得我們所有人的生日,包括女婿和兒媳。

我們以爲生活會就這樣波瀾不驚卻也美好地一直繼續下去,雖然理智告訴我們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但我們不敢想象生活突然停止和破碎的時刻,盡管這樣的時刻我們早已經曆過。
父親年輕時是個帥哥,家教好、相貌好、有文化又多才多藝。他是我們韓氏家族的長房長孫,據說我太祖父脾氣暴躁,對自己的兒女非常苛責,但對這個孫子卻是無比疼愛。祖父祖母就這一個獨生兒子,更是從來舍不得說一句重話讓他吃一點苦。所以說父親生來是個好命的人!
父親善良仁厚,願意幫助人,年輕時身上還散發著文藝氣息,聽母親編排說村裏幾個出挑的姑娘都暗戀父親,有的以父親爲擇偶標准,結果耽誤到了三十幾歲了也沒嫁出去,最後不得不面對現實。
曾經爲了找一個日記本,我開過父親的小箱子,偷看過父親的日記,那文字充滿激情,大多是要把青春獻給鄉村教育事業的誓言和決心,完全符合那個時代的特征,裏面還有很多父親寫的詩,當然那些詩句現在看來詩味不是很濃,文學性也不是很強,大多是直抒胸臆的。
但父親看起來是個內向的人,他平時並不愛說話,波瀾不驚的,因爲父親的沉默,我們幾個小孩子都很怕他,後來年紀漸長,我明白了,其實父親是個簡單的人,他單純而且浪漫,是他的不愛說話成功掩飾了他的單純,顯得成熟穩重,實現了與校長身份的匹配。
父母的婚姻是包辦的,這是母親的說法。因爲小時候母親每次跟父親吵架,都要數落一個叫周老七的人,說都是周老七沒做好事造的孽。後來我知道了周老七是父母婚姻的媒人,這個倒黴的牽線人不知道被人家埋怨了多少年,估計還以爲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呢。
母親的老家是邊外蒙地(俗稱,實際指遼西柳條邊以外蒙古族聚集區)的,我的外祖父是邊蒙一帶的名人,各方勢力的糾紛都會找我的外祖父擺平,但他四十幾歲就因爲霍亂去世了。我的外祖母性情溫厚,卻特別能幹,她的娘家勢力強大,有白道當官的,有黑道綠林的,所以外祖父去世後,她一個寡婦守住了偌大的家業。
母親聰明好學,但她卻不是父親那樣好命的人,剛出生就沒了父親。20世紀60年代初,因爲社會原因,她從正在讀書的沈陽某高校辍學,經過那個周老七的介紹(是外祖母委托的周老七),嫁給了個人條件和家境尚好的我父親。現在想來,母親估計也是一個顔值控,一見面就被我父親迷住了,把責任都推給周老七也是有失公允的。
母親自小沒有父親,她的母親和比她年長許多的兄姐就對她格外嬌慣,母親是任性和強勢的,她和父親兩個從小被寵大的人在一起,難免會起沖突。在漫長的鬥爭中,父母都老了,老了的父親在母親的強勢下選擇了忍讓和裝聾作啞,母親行走不便後,更是鞍前馬後悉心照料。
我曾對我的妹妹說,母親其實內心是柔軟脆弱的,她渴望愛和被關注,她離不開父親,只是她沒有學會如何正確表達自己的情感,她也羞于承認和表達自己的情感,這應該與她從小不完整的原生家庭有關。
母親和父親一起生活了六十年,也吵吵鬧鬧了六十年,這一切都在2023年10月7日那個清晨結束了。去年10月,國慶和中秋假期趕在了一起,我們姐妹兄弟五個都回了老家,父親騎著電動車一次次去村裏的集市買菜。父親願意趕集,趕集是父親晚年差不多唯一的娛樂活動。那一次父親煎炒烹炸給我們准備了一大桌子飯菜。晚飯後,我和妹妹用輪椅推著母親走過街街巷巷,街面上堆滿了金燦燦的玉米棒子,那晚的月亮真是大又圓。
我和妹妹兩個年過半百的女兒,吃過八十歲父親做的飯菜,再推著八十歲的母親看風景,暮色四合中的故鄉裏,天上的一輪滿月,照著地上的幸福,一切都是那麽美,那麽圓滿,也那麽的不真實。

人是有局限的生命,你永遠無法預知下一秒會發生什麽;人也是幻覺動物,而生活的真相是殘酷的。比如我們以爲會永恒的友誼和愛情,比如我們以爲會永遠陪伴我們身邊那些人,在活著的過程中,我們會突然發現,這世界上沒有一件恒常的事物,一切都在我們無法把握的變化中,我們終其一生都在告別,與青春,與友誼,與愛情,與親人,與自己曾擁有的一切。
四
假期結束開始上工的那個清晨,父親就突然走了,跟母親說說話就走了,走得平靜安詳。
父親走了,母親頓時失了魂魄,我們把母親接到城裏,妹妹們悉心照料,母親才慢慢緩過神來,緩過神來就要回家,她不能舍下她和父親共同生活了幾十年的那個家,她得守著,不能讓父親的家沒了,更不能讓她的孩子們無家可歸。何止是母親,我一想到那個溫暖明亮的老屋和幹淨整潔的院落,那個盛滿了我們無數記憶的家,最後因爲父親的離去,要變成一座廢棄的宅院,而我回故鄉的理由可能也就只剩下每年清明的祭掃了。完整的生活破碎至此,又怎能不心痛?
原來人無論多大年紀,都需要一個故鄉,需要一個有父母守著的老家。
這個老家當初是我自己立志離開的。我作爲一個早慧的孩子,從小我就想得跟小夥伴們不一樣。我要離開,離開鄉村,離開這個村子一輩輩人的生活模式,我不能被一個村莊困住,不想在長長的地壟溝裏完成自己的一生。那時候覺得無數的遠方都在向我招手,遠方的燈火有著無盡的誘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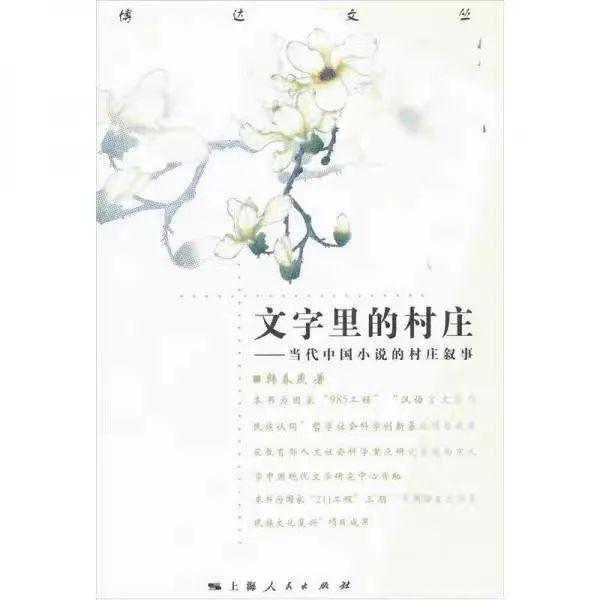
出走四十年,現在的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有些東西是走不出去的。這四十年,那個村子一直都在我身邊,它在我的血液裏,在我的靈魂中,我當年是帶著它上路的。我帶著它跋山涉水,見識過城市的繁華與喧囂,感受過人性的明亮與幽暗,體驗過人情的冷與暖,雖然我在時光中變了容顔,但曆經滄桑之後,心底裏仍是那個鄉村的少年。
我混迹城市幾十年,卻仍然喜歡野地和植物,喜歡遼闊和壯麗,喜歡自由和散漫,不喜歡生鮮超市,喜歡逛農貿市場。我無法精致,也學不來高雅,甚至連研究的專業方向都是鄉土文學。野地的女兒,需要回到自由的風裏。即使當演員估計也只能扮演個地主婆,卻無法扮演一個貴婦人。也許,這就是鄉村賦予我的DNA。
我是一個幸運的人。我出生在鄉村,我擁有故鄉和故土,我能找到我的根。我四十多年前以爲斷掉的臍帶還在,故鄉還在爲我輸送養分。在鄉下我還有老宅,那裏有我童年少年全部的記憶,有我的爺爺奶奶對我的愛。也許有一天那座老宅不複存在,也許有一天我與故鄉之間只剩下一個夢幻般的記憶,可那又如何呢?一切畢竟發生過、存在過,生命的曆程不就是不斷的丟丟揀揀嗎?這無疑讓人悲傷,而悲與歡這就是人生啊!
我感謝命運,感謝故鄉,那個邊蒙交界之地普普通通的村莊,我從那裏來到這個世界,我用十幾年的努力離開它,後來又用了幾十年來返回它——沿著生活、學術、文學等各個路徑。
願故鄉安好!願祖父祖母父親安息!
作者:韓春燕
作者簡介

韓春燕,文學評論家。現任遼甯省作協副主席,遼甯省作協理論與批評委員會主任,遼甯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東北文藝振興研究院院長,《當代作家評論》雜志主編。1980年代開始發表詩歌和小說。主要從事鄉土文學和現當代作家作品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省社科基金項目等二十多項,發表學術論文200多篇,出版學術專著4部。
